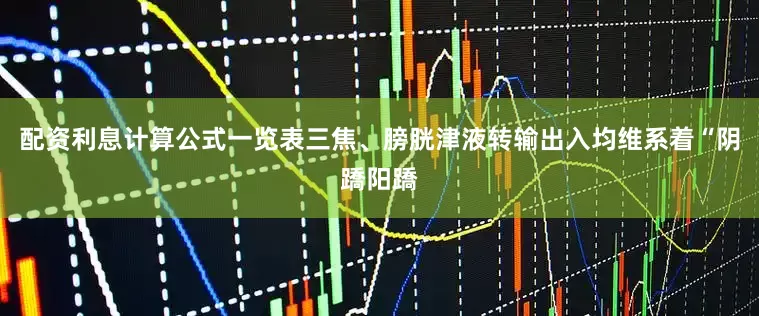
慢性失眠
使用安眠药治疗慢性失眠固然能令人进入睡眠状态,并持续数小时不等的时程,觉醒后常常达不到获得自然睡眠的效果。于是便产生一个临床问题:安眠药发挥药效所取得的进入睡眠状态和持续的时间,与自然进入睡眠状态和睡眠过程是相同的吗?
尽管临床和试验采用模拟自然睡眠状态的多种疗法,或许有些疗法模拟自然睡眠的生理机制,但仍然达不到自然睡眠与自然觉醒的临床效果。迄今,自然睡眠和自然觉醒的生理机制仍在探索之中。慢性失眠的特征有两个方面:①进入睡眠状态障碍;②睡眠过程和睡眠时间与自然睡眠过程和自然觉醒时间存在显著差异。那么,无论用化学方法或是物理方法,处理慢性失眠需要回答三个问题,即睡眠状态、睡眠时间和自然觉醒时间。
首先,《内经》论述自然睡眠状态、自然睡眠过程和自然觉醒的术语是“寤”“寐”。自然睡眠状态和自然睡眠时程称为“目瞑”,自然觉醒状态称为“昼精”。睡眠状态障碍称为“目不瞑”“目瞋”,睡眠过程障碍称为“不得安卧”,非自然觉醒状态称为“昼不精”。经文所强调的睡眠状态和睡眠时程是一个循环有序的自然更替过程。于是在讨论失眠时,常常论述营卫循行的昼夜规律,阳蹻脉与阴蹻脉的离合,阳气的盛衰,精血的盈亏。其次,《灵枢·营气》与《灵枢·卫气》中营卫在经脉中有序更替的理论,气血盈亏的自然规律,均与自然界的日月运行规律密不可分。这个显著的特点是强调睡眠的自然状态和自然时程。慢性失眠的目标疗效是恢复自然睡眠状态、自然睡眠时程和自然觉醒状态,即经文所说的昼精而夜寐。
目前临床治疗慢性失眠存在的难点:①昼夜寤寐与营卫行于阴、行于阳关联,但不相关,营卫运行规律只能部分解释寤寐节律的形成。②“心主神明”,但心主神明解释慢性失眠与神志疾病尚待区别。③“膻中者,喜乐出焉”。膻中与髓海(大脑)的关系能否用精化气,气生精,气生神的机制解释。慢性失眠临床期望疗效目标:①昼夜规律周期;②适应性充足睡眠时间;③充沛体力和精力;④记忆力改善;⑤乐观情绪。
我们重温经文的原创思路发现:邪气内入是始动因素,肾气不充、胃气不和是基础因素,蹻脉失调是基本病机,气血逆乱是睡眠节律紊乱基本特征。此外,睡眠多梦属于神不守位。治疗方法诚如《灵枢·邪客第七十一》说:“补其不足,泻其有余,调其虚实,以通其道,而祛其邪。此所谓决渎壅塞,经络大通,阴阳和得者也”。《素问·异法方异论第十二》说:“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也。”
第一节 阴阳盛衰失常是慢性失眠的主要特征
一、蹻脉阴阳相交是自然睡眠和自然觉醒更替规律的始动因素
【经文】
1.阳气尽,阴气盛,则目瞑;阴气尽而阳气盛,则寤矣。(《灵枢·口问第二十八》)
【注释】
①阳气:卫气(Defensive Qi)。
②阴气:营气(Nutrient Qi)。
③尽:卫气行于阴蹻脉、行于阳蹻更替时序。
④寤寐:寤与阳合,寐与阴并。
【解读】
(一)营卫协和自稳状态是寤寐交替的基础因素
经文称自然睡眠时程和自然睡眠状态为“瞑”,自然觉醒为“寤”,寤寐有序更替是指自然睡眠时程、自然睡眠状态和自然觉醒的更替,表明瞑与寤更替是有明确的时间顺序的。自然睡眠和自然觉醒皆源于阴阳盛衰更替,经文称阴阳盛衰更替为“盛”和“尽”。一方面,经文昭示这种阴阳盛衰更替规律源于机体内环境阴平阳密的自稳机制;另一方面,《灵枢·营卫生会第十八》说:“营在脉中,卫在脉外,营周不休,五十而复大会……卫气行于阴二十五度,行于阳二十五度,分为昼夜……太阴主内,太阳主外,各行二十五度,分为昼夜。”马莳注:“营气随宗气以行于经隧之中,始于手太阴,而复大会于手太阴,此太阴之所以主内也(此营气之行源于《灵枢·营气第十六》)。卫气不随宗气而行,而自行于各经皮肤分肉之间,始于足太阳,而复会于足太阳,此太阳之所以主外也。营气、卫气各行于昼二十五度,各行于夜二十五度,分为昼夜,各为五十度……营卫之行,如是无已,真与天地同其运行之纪也。”同篇经文上文说:“卫气昼日行于阳,夜半则行于阴,阴者主夜,夜者主卧。”表明机体内环境自稳对于昼夜交替节律的适宜性。这是经文从机体内环境自稳调节机制以及对昼夜节律的适宜性认识睡眠启动机制的阐述。
《灵枢·脉度第十七》说:“(阴)蹻脉者,少阴之别,起于然骨(照海穴)之后,上内踝之上,直上循阴股入阴,上循胸里入缺盆,上出人迎之前,入[插图],属目内眦,合于足太阳、阳蹻而上行,气并相还,则为濡目,气不营则目不合。”《内经》没有记载阳蹻脉的起止,阳蹻脉的起止见于《难经·二十八难》:“阳蹻脉者,起于跟中(足太阳经申脉穴),循外踝上行,入风池。”《难经·二十六难》说:“阳络者,阳蹻之络也;阴络者,阴蹻之络也。”《四明心法》说:“阳蹻之络统诸阳络,阴蹻之络统诸阴络,脾之大络,又总统阴阳之络,由脾之能溉养五脏也。”《难经·二十九难》说:“阴蹻为病,阳缓而阴急;阳蹻为病,阴缓而阳急。”《难经经释》注:“阳脉弛缓而阴脉结急,阴脉弛缓而阳脉结急也。蹻者,蹻捷之义,故其受病则脉绞急也。”由此可知,阳气盛衰与阳蹻脉关联,精血盈亏则与阴蹻脉关联。有理由认为,寤寐更替与阴蹻脉、阳蹻脉功能存在关联性,故张景岳说:“目之瞑与不瞑,皆蹻脉为之主。”
营卫谐协是维系二蹻功能的重要因素。首先,《素问·生气通天论篇》说:“阳气者,若天与日,失气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是故阳因而上,卫外者也。”《灵枢·禁服四十八》说:“卫气为百病母”。可见经文所说的“阳气”当是指“卫气”。其次,《灵枢·营气第十六》说:“营气之道,纳谷为宝,谷入于胃,乃传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周学海注:先统营卫而言),其精专者,行于经隧(周学海注:折入营气),常营无已,终而复始,是为天地纪”。《内经》只有“营气”术语,并没有“营血”术语,此条经文所说的“阴气”当是指“营气”。陈潮祖教授认为“经隧”是指:“五脏是由肝系筋膜构成的五条大小不同的管道,与五脏连成五系,再由三焦将五系连成一体,上连于脑,而以脑为主宰,成为经脉、经筋、经隧弛张(loose and tight)运动发号施令中枢”,可知营卫失调则可导致“经隧”弛张运动发号施令中枢失常。第三,营卫谐协维系二蹻脉的盛衰,营卫失谐协,卫气或留于阴,或留于阳,均导致三阳经或三阴经营血渗灌奇经失常,从而引起二蹻脉缓急病证。故《灵枢·大惑论》说:“卫气不行于阴,常留于阳,留于阳,则阳气满,阳气满则阳蹻盛,不得入于阴,则阴气虚,故目不瞑矣。”又说“卫气留于阴,不得行于阳,则阳气虚,故目闭也”。故张景岳注:“ 凡人之寤寐,由于卫气。”有理由认为,营卫失调、二蹻脉之缓急在慢性失眠发生发展病程中是经常起作用的重要因素。卫气之行迟速,其或行于阴、或行于阳均是阴阳盛衰更替的始动因素。
(二)气血虚实与昼夜节律适应性是维系自然睡眠时程的重要因素
日之寒温、月之虚盈与四时气之浮沉、昼夜节律密切相关。《灵枢·营卫生会》阐述了营气、卫气各行二十五度,分为昼夜,揭示营卫循行内环境的自稳调节不但与昼夜节律相适宜,而且日月的运行规律也影响机体的气血盈虚。《素问·离合真邪论第二十七》说:“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涩;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卒风暴起,则经水波涌而隆起。”《素问·八正神明论第二十六》说:“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郭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郭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是因天时而调气血”。日月的运行规律与睡眠和觉醒的两种自然状态密切相关,其昼夜节律既是启动自然睡眠机制的重要因素,又是参与机体气血调节的因素。首先,经文回答了自然睡眠和自然觉醒的原因是气血虚实的有序节律,若机体气血盛衰的节律紊乱则发生昼不精而夜不寐。其次,气血盛衰的节律紊乱则可发生营卫失调,由此而导致血虚生热则邪并于阳;卫气失常则邪并于阴。正如《素问·八正神明论》所说:“以身之虚,而逢天之虚,两虚相感,其气至骨,入则伤五脏”。正因为气血盛衰节律紊乱与昼精夜寐关系密切,所以临床所见血气失和病证经常伴有短暂寤寐更替失调,或目不瞑,或卧不安,或夜眠多梦,或夜寐时醒,或倦怠多寐等诸多夜不寐现象。临床更多见到是慢性失眠往往合并几乎所有脏腑、经络病证,这些脏腑、经络病证均与气血、寒热、虚实病证存在密切或直接相关性。
由于自然睡眠和自然觉醒与昼夜节律、机体营血卫气的自稳功能状态密切相关,机体对昼夜节律的变化有其自适宜性。因此机体营血卫气的自稳功能状态在自然睡眠和自然觉醒的节律循环过程中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其营卫气血的虚实与年龄、性别和脾胃功能状态直接相关。卫气营血不和不但可以导致自然睡眠和自然觉醒有序更替的节律紊乱,也可以导致“惊狂”之类的精神、神志类病证。“气并于阳”多“风、火”;“血并于阴多“寒、湿、痰饮”。血虚生热则邪并于阳;卫气不足则邪并于阴。《素问·调经论》说:“气血以并,阴阳相倾,气乱于卫,血逆于经,血气离居,一实一虚。血并于阴,气并于阳,故为惊狂”。《太素》注:“血并则血有气无,气并则气有血无,是以言虚不无其实,论实不废有虚,故在身未曾无血气也。所言虚者,血气相并,相失为虚,相得为实耳。”
【经验方】防己地黄汤(《金匮要略》)化裁
防己9g 防风9g 桂枝9g 炙甘草9g 黄芩12g 生地黄50g 姜半夏12g生薏苡仁20g 生姜9g 红花6g 僵蚕9g 全蝎3g
证候目标:长期寐差多梦,或彻夜不寐,头晕头痛,精神萎靡,或表现荒唐反常的动作,自言自语,或强迫症,无恶寒和发热。舌红少苔,脉浮或数。
(一)方解
《金匮》中防己地黄汤原方治疗如狂状,妄行独语。妄行、独语皆为肝气实而生内风,热在内而外无热,其脉浮乃为热耗其血,血虚则营气不充,而卫气独治,故其脉浮而已,因此仲景认为“浮者血虚”!由此可知,妄行、独语不休揭示了“肝藏血,血舍魂”的临床征象。《兰台轨范》说:“此方,他药轻而生地独重,乃治血中之风也。”提示育阴涵阳,调燮营卫有镇静安神的临床效果。防己、防风、桂枝、炙甘草轻清归于阳,生地黄甘寒归于阴。全方功效:调燮阴阳,镇静安神。有理由认为,防己地黄汤有镇肝平惊、安神定惊的作用,是可以用于治疗失眠的。
(二)临床应用
慢性失眠常见的问题是伴有程度不同的神经官能症,主要以抑郁和焦虑为主,甚至表现为精神障碍和人格变异,长期不规律服用镇静催眠药物甚至服用抗抑郁焦虑药物维持夜间睡眠。慢性失眠治疗难度首先在风、火、痰、湿、食、寒诸邪错杂相间的致病因素的处理。其次是“血气不和”所形成的虚实并存证候的调适。慢性失眠的治疗原则当遵循《素问·异法方异论第十二》所说:“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也。”防己地黄汤给予失眠临床的启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从心主血脉考虑:交加散(生姜、生地黄)出自《普济本事方》原方治疗产后中风,营卫不通,经脉不调。着眼点在调气血。这与治疗“心动悸,脉结代”名方炙甘草汤中重用生地黄是相似的配伍原则!
2.从祛邪方面的考虑:①半夏、生薏苡仁仿效《灵枢》半夏秫米汤,原文称其功效为“决渎壅塞,经络大通”,用生薏苡仁替代秫米。②慢性失眠需要考虑“久病入络”病机。温经活血是否可以有强神的作用呢?《妇人良方》在原方基础上加肉桂、白芍、当归、红花、炙甘草、 蒲黄、没药、苏木,治疗营卫不和,月经湛浊等。其病机着重点在寒邪阻络,《日本经验方》记载强神汤治疗脑卒中(红花、僵蚕、棕榈、甘草),提示温经活血通络有镇静安神的作用!结合这两个方剂组成,我们认为在防己地黄汤内加入红花可以增强镇静疗效,加入少量僵蚕可以增强生地“通血痹”的功效。
二、蹻脉阴阳相交维系着自然睡眠和自然觉醒有序更替
【经文】
2.阴蹻阳蹻,阴阳相交,阳入阴,阴出阳,交于目锐眦,阳气盛则瞋目,阴气盛则瞑目。(《灵枢·寒热病第二十一》)
【注释】
①阴蹻脉:《灵枢·脉度第十七》曰:“蹻脉者,少阴之别,起于然骨之后,上内踝之上,直上循阴股入阴,上循胸里,入缺盆,上出人迎之前,入[插图],属目内眦,合于太阳阳蹻而上行,气并相还则为濡目,气不荣则目不和。”
②阳蹻脉:《内经》没有记载阳蹻脉的循行。但在《难经·二十八难》中有记载,其曰:“阳蹻脉者,起于跟中,循外踝上行,入风池。阴蹻脉者,亦起于跟中,循内踝上行,至咽喉,交贯冲脉。”
③阳气盛,阴气盛:盛:盛行(exuberance)。
【解读】
(一)太阳膀胱经、少阳胆经和三焦经气血盛衰与二蹻脉缓急密切相关
经文此处强调阴阳盛衰与离合部位是在阴蹻脉和阳蹻脉。阴蹻脉涉及少阴肾经和冲脉;阳蹻脉涉及太阳膀胱经、少阳胆经和三焦经。阴蹻阳蹻均起于足跟,皆至目内眦。张志聪于此条经文注释说:“此言足太阳之气贯通于阳蹻、阴蹻也。莫云从曰,足少阴、太阳乃阴阳血气之生原,阴蹻阳蹻主通阴阳血气,从下而上交于目。目者,生命之门也。”由于阳蹻乃足太阳之别脉,阴蹻乃足少阴之别脉,胞中为血海,膀胱为津液之腑,肾主藏精,皆有流溢于中之精血贯通,故营气之不荣于任脉二蹻。《灵枢·本脏第四十七》说:“肾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应。”《素问·热论篇第三十一》说:“巨阳者,诸阳之属也,其脉连于风府,故为诸阳主气也”。王冰注:“太阳之气,经络气血,荣卫于身,故诸阳气皆所宗属。”这表明阴蹻阳蹻渗灌疏浚调节足太阳、少阴阴阳气血盈亏。《灵枢·邪客第七十一》“卫气独行其外,行于阳,不得入于阴。行于阳,则阳气盛,则阳蹻陷,不得入于阴,阴虚,故目不瞑。”此非卫气行于二蹻,乃其气留于三阴或三阳,过满而溢入蹻脉,与《难经》所谓“沟渠满溢,流于深湖”其义相同。显然,卫气之行,有迟有速,其气剽悍滑利,并非限于一定时刻。卫气行于阴、行于阳参与“阴蹻阳蹻,阴阳相交,阳入阴,阴出阳”的寤寐节律调节。而“卫气独行其外,行于阳,不得入于阴”则是寤寐节律失调的启动机制。故张景岳说:“凡人之寤寐,由于卫气。”
由此可知,卫气之行失常是经脉气血盛衰更替的始动因素。“阴蹻阳蹻,阴阳相交,阳入阴,阴出阳,交于目锐眦”所揭示的是机体自然睡眠和自然觉醒有序节律而出现昼精而夜寐征象。卫 气之行或迟或速,留于经脉导致三阴三阳经气血盛衰失调,其气血渗溢于奇经八脉失常而出现“沟陷渠沮”,以致二蹻脉或纵缓或挛急,从而引起睡眠与觉醒更替节律紊乱而出现瞋目不合与瞑目不开征象。由此《 太素》注:“今于目眦言阴阳出入,以相交会目得明也。所以阳盛目张不能合,阴盛则目瞑不得开,宜取此二蹻”。进而言之,胆疏泄和敛降,三焦、膀胱津液转输出入均维系着“阴蹻阳蹻,阴阳相交,阳入阴,阴出阳”的有序节律更替。显然,胆、三焦、膀胱气血津液病证多伴有阴蹻阳蹻“阴阳不相交”之“目不瞑”“卧不安”“昼不精”“夜不寐”诸多失眠征象。如果从慢性失眠的征象解读,则“瞋目”是强调进入睡眠状态障碍,“瞑目”突出自然觉醒障碍。如果从自然睡眠解读,则“目瞑”是指睡眠状态,“瞋目”是觉醒状态。判断是处于睡眠和觉醒节律紊乱,还是自然睡眠与自然觉醒的关键点在“阳气盛”和“阴气盛”是否处于自然有序更替的状态!精血盈亏与阴蹻脉相关联,而阳气的盛衰与阳蹻相关联。阴蹻脉异常的原因是精血亏虚,而阳蹻脉的异常多有邪气之扰,且多伴有气机升降失调和气血津液出入紊乱。
《素问·痹论》说:“卫气者,水谷之悍气也,其气慓急滑利,不能入于脉也,故循皮肤之中,分肉之间,熏于肓膜,散于胸腹。”揭示上下之气莫不由三焦升降,表里之气莫不由三焦出入,故三焦不仅是卫气运行之所,也是水液升降出入之区。慢 性失眠由卫气独行于外,行于阳,不入于阴所形成的卫气病变,既有致胆气疏泄和敛降失调,又有三焦水道失调或气化不利,呈现津气同病和膜失柔和,并引起二蹻脉的纵缓、挛急,呈现“目瞋不合”或“目闭不开”征象。由此可知,卫气病变并发津气同病,膜失柔和均可以发生慢性失眠。显然,这与少阳病小柴胡汤证的正气不足和邪气侵袭,气郁化热和津凝为湿,清阳不升与浊阴不降的征象和病机存在重叠。这一点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通过散结内外之邪,降上冲之气,理气行水,治疗胸满烦惊,昼夜不眠,易惊、焦虑易怒、易动感情、善叹息,甚至出现狂乱、痉挛等病证疗效也已经得到临床证实。这就可以部分解释慢性失眠为什么多伴有太阳膀胱、少阳胆和三焦病证的原因。因此,“清、疏、通、利”也是有效治疗慢性失眠的方法之一。
(二)膻中者喜乐出焉、心者神明出焉均参与慢性失眠的发生发展
“目闭不能开”“目开不能合”均是二蹻脉或缓或急征象。同时,目的开合又是心主神明的外在征象。慢性失眠常伴有与情绪和神志相关的病证征象多源于七情所伤,而七情所伤所出现的焦虑、烦躁、抑郁、烘热、出汗、健忘、甚至喜怒无常,亦无不与心不藏神,神不守位相关。《素问·解精微论八十一》说:“心者,五脏之专精也,目者,其窍也。”“志(mind)与心精(refined essence),共凑于目也。”《灵枢·大惑论第八十》说:“目者,五脏六腑之精也,营卫魂魄之所常营也,神气之所生也。”《素问·灵兰秘典论》说:“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heart governing mind and spirit)”,提示心神通于目窍!《灵枢·邪客第七十一》说:“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脏坚固,邪弗能容也。诸邪之在心者,皆在于心之包络。包络者,心主之脉。”《素问·刺法论第七十二》说:“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可刺心包络所流。”揭示神志类的病证与寤寐节律失调病证的各自病机不同,但却存在着诸多征象重叠!符合慢性失眠者伴有神情或抑郁、或烦躁、或多虑等神志失调临床表现。此外,《金匮》所记载的“欲卧不得卧,欲行不得行……如有神灵”的百合病(lily disease)则描述了睡眠过程障碍的临床征象。这也解释了临床采用镇静安神、养血安神之类药物应用于慢性失眠临床的依据,同时也指出诸多安神治法为什么治疗慢性失眠的疗效不尽如人意的原因。另一方面,膻中(气海或宗气,喜乐出焉)、心与心包(神明出焉)的功能无不与脑(髓海,神明之腑)相关,而“经隧”则是三者之间的联系通路!陈潮祖教授著《中医治法与方剂》中认为经隧为筋膜,并解释为“五脏经隧由筋膜构成,是气血津液精摄纳、生化、疏泄之所。”其研究结论为“肝系筋膜,本属脑系,脑外膜络即为心包络”。诚如《灵枢·玉版第六十》说:“经隧者,五脏六腑之大络也。”
慢性失眠的目标疗效是恢复机体自然睡眠和自然觉醒的节律,即经文所说的昼精而夜寐。寤寐是心主神明的外证表现,心主神明亦在阴蹻阳蹻、阴阳相交的节律中发挥调节作用。维系“营卫之行,上下相贯,如环之无端”的昼夜节律源于肺胃肾气血盛衰。《灵枢·动输第六十二》说:“手太阴、足少阴、阳明独动不休。”马莳注:“肺脉动之不休者,以营气随宗气行诸经,其诸经之脉朝于肺也。胃脉动之不休者,以卫气出于胃而行之不已也。肾脉动之不休者,以冲脉与肾脉并行,而行之不已也。”由于自然睡眠和自然觉醒与昼夜节律、机体营血卫气的自稳功能状态密切相关,因此机体营血卫气的自稳功能状态在自然睡眠和自然觉醒的节律循环过程中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营卫失和则导致阴蹻阳蹻出现纵缓、拘挛,由此而导致阴阳相交,阳入阴、阴出阳的节律紊乱,其病机表现为卫病不得合于营,故目瞑则卫气无归;营气缭乱,亦不归经,故发目瞑心烦;卫气独行于阳,不与营谐协,则目瞋不合。故营卫不谐协的临床征象呈现为昼不精而夜不寐。因此,调营和卫,养心安神是治疗慢性失眠不可或缺的方法。当入睡困难、夜寐时程延长得到改善时,尤须检测是否获得自然睡眠状态(指多梦、呓语、卧不安)和自然觉醒疗效。
【经验方1】百合蠲忿汤
百合20g 夏枯草12g 茯神12g 合欢皮12g 生地黄20g 北沙参15g竹茹12g 郁金12g 苍术12g 香附6g 陈皮6g 菟丝子12g
目标证候:神情困倦却入睡困难,或似睡非睡,头昏沉而健忘,颈以上多汗,胸膈烦闷,头热足冷,腹满,夜尿频而量少。舌质红,舌苔薄少,右脉浮而弦无力,左脉关弦有力,尺沉。
(一)方解
百脉合之于肺,藉百合之清金,能开能合,开其肺使百脉合于肺,复由合而分,回复循环,与生地濡润营血之燥以通血痹,二者合用排泄瘀热;菟丝子合茯神又名交感丹出自《普济方》以升降水火。香附合茯神也名交感丹出自《洪氏集验方》主治情志不遂,胸膈痞闷。解郁安神,配伍夏枯草、合欢皮、香附、茯神、陈皮、郁金增强解郁安神,协以苍术通调脾胃,陈皮、沙参、竹茹和胃降逆,《素问·阴阳类论七十九》曰:“二阴至肺,其气归膀胱,外连脾胃。”
(二)临床应用
此目标证候的特征主症是昼不精而夜不寐,而次症以“志意通,内连骨髓(《素问·调经论》)”障碍的心烦、头昏沉和健忘。首先,营血不充而血不舍神,卫气独行于阳而不入于阴,其征象呈现为神情困倦却入睡困难,或似睡非睡,故其病机表现为营卫失于谐协。其次,卫气并于上,其征象呈头烘热,颈以上多汗,胸膈烦闷;营血并于下,其征象呈头昏沉而健忘,足寒,腹满,夜尿频而量少。此上热下冷征象正是仲景所说的少阴厥阴证临床征象,故病机表现为气机升降失调。肾主静与卧,肾不和则神情倦怠,似睡非睡,仲景称“常默然”。夜尿频而量少伴随健忘、心烦、头昏沉、腹满则并非是肾与膀胱失职,而是属于肝所生病为遗溺闭癃。
【经验方2】定坤散
柴 胡24g 黄芩9g 姜半夏9g 太子参12g 炙甘草6g 桂枝6g 牡丹皮6g 生白芍12g 生白术12g 泽泻15g 猪苓12g 生地黄15g 生牡蛎20g
目标证候:素有神经性头痛。寐差多梦,头面时觉烘热,胸部以上汗出,急躁易怒,多语,肢体烦疼,小便不利。脉弦有力,舌质淡红,舌苔薄白根部垢浊。
(一)方解
柴胡桂枝汤合五苓散加牡丹皮、生牡蛎治疗围绝经期卵巢功能退化所引起的烘热,胸以上汗出疗效显著。同时伴随的慢性失眠和顽固性头痛也获得显著改善。其药物配伍为:①半夏、生姜、黄芩降泄浊阴;②柴胡、桂枝升发清阳;③炙甘草、大枣、丹皮、白芍、生地缓和膜络;④茯苓、牡蛎、泽泻、猪苓调其津液;⑤太子参、白术、炙甘草、大枣培补元气。组方的基本原则源于傅青主的定经汤。定经汤以当归、白芍以补肝血而柔风木,此方以白芍、炙甘草、生地、丹皮凉肝益阴。定经汤以菟丝子、熟地以益肾精而养冲任,此方以生地、太子参益气养阴以资金行清化而水自长流;定经汤以柴胡、荆芥之芬芳,以舒肝郁,此方以小柴胡汤疏解少阳之郁结;定经汤以山药、茯苓之甘淡,以利肾水,此方以五苓散温阳化气利水,可见此方效仿定经汤,以疏利气机,通调三焦,畅行津液之道,从而达到气行津行,二蹻二维渗灌气血津液有节,以致任脉通,冲脉盛,而经水如潮水有期。这也是此方以柴胡桂枝汤合五苓散加味而取名“定坤散”的原因所在。
(二)临床应用
目标证候主症为寐差多梦,烘热,胸以上汗出;次症为急躁易怒,多语,小便不利,肢体烦疼。此证仅见于40岁以上的女性,既往有神经性头痛和月经先后无定期病史。首先,临床证实五苓散治疗中年女性顽固性头痛的可靠性,可以认为膀胱气化不利也是引起顽固性头痛的病因之一。其次,傅 青主阐述月经先后无定期病机时说:“妇人有经来续断,或先后无定期,人以为气血之虚,谁知是肝气之郁结乎!夫经水出诸肾,而肝为肾之子,肝郁则肾亦郁,肾郁而气必不宣,前后之或断或续,正肾之或通或闭耳。肝气之或开或闭,即肾气之或去或留,相因而致,又何疑焉?”第三,由于阴蹻脉虚实与少阴肾经和冲脉密切相关,傅青主说“经水出诸肾”。而冲脉的盈虚与月经的期、色、量、质密不可分。由此可知,肝气郁结是卫气之行,行于阳而不入于阴的始动病因!其气滞津凝是其主要病机。虽然有时伴有口干咽燥,饮水多等津液不足表象,但病机重心在少阳枢机不利,三焦气滞,津液不行,其征象表现为舌质淡、苔薄白根垢浊,头痛、口渴而小便不利,脉弦有力。因此“清、疏、通、利”仍然是其基本治疗方法。
【经验方3】凉血清神汤
黄芩15g 苦参12g 生地黄30g 生大黄3g 焦栀子6g
目标证候:顽固性失眠,手足烦热,或足掌热而欲覆冰冷却,口渴数饮,颜面潮红,或心烦卧起不安,大便灼肛,小便不利。舌质红,苔薄黄,脉沉弦数而有力。
(一)方解
《长沙药解》说:“甲木清降,则下根癸水而上不热,乙木温升则上生丁火而下不热,足厥阴病则乙木郁陷而生下热,足少阳病则甲木郁升而生上热,以甲木原化气于相火,乙木亦蕴含君火也。黄芩苦寒,并入甲乙,泻相火而清风木,肝胆郁热之证,非此不能除也”。《经证证药录》说:“生地黄甘寒滋润,能降上炎之火,清燥热之土,溢虚耗之精,润枯槁之木,使并上之阳,下交于阴……经方以苦参治咽干,小便难……苦参能降肺气,清肝热,下心火,以通冲任之原,故为血分湿热,冲任之要药。”方中用苦参配伍功效如《别录》所言:“去伏热”,并非取其杀虫。据大冢敬节临床实践,顽固性失眠患者如有颜面潮红、烘热和不安感用三黄泻心汤效果显著,而我们在实践中,栀子大黄汤与三物黄芩汤合用则慢性失眠疗效更佳。仲景以三物黄芩汤治疗产后失血而致手足烦热,其病机又称为血分伏热。此证的病机为阴血亏损,阴不胜阳,热蕴于阴血。《素问·评热病论第三十三》说:“胞脉者属心而络于胞中”。《素问·骨空论第六十》说:“冲脉为病,逆气里急。”吴昆注:“热则逆气,寒则里急。”由此可知,产后失血,阴不胜其阳所引起的手足烦热当并发失眠,逆气上冲所导致的心烦卧起不安、颜面烘热等征象。
(二)临床应用
1.夜不寐、烦热、卧起不安是慢性失眠经常遇到的问题,尤以心、肝、肾热象多见。所谓心、肝、肾热证皆由内蓄而发于外,因脏腑之用各有所偏,物性之殊,久而增气,心、肝、肾热象则随体禀多热之经而发有定处,热邪随五脏所合而舍于其所合,其热象表现亦各有不同。显然,内生热证不同于外感寒邪之传经化热及温病之伏气变温。《素问·刺热篇第三十二》说:“肝热病者,小便先黄,腹痛,多卧,身热,热争则狂言及惊,胁满痛,手足躁,不得安卧……心热病者,先不乐,数日乃热,热争则卒心痛,烦闷,善呕,头痛,面赤,无汗……肾热病者,先腰痛[插图]酸,苦渴数饮,身热,热争则项痛而强,[插图]寒且酸,足下热,不欲言。”经文所言心热、肝热、肾热之“身热”,与发热不同,病者但觉烦热在体,而不似发热外蒸之状,虽热必不恶寒,但热邪之在血分是其共同的病机。热留营血,脉流薄急,一方面发生“气血以并,阴阳相倾,气乱于卫,血逆于经,血气离居,一实一虚。血并于阴,气并于阳”;另一方面,心合于脉,脉为血府,凡热入血分,即易循脉内陷,心包代心受邪,其热移于肝胆,则出现“大筋[插图]短,小筋[插图]长”,从而发生二蹻脉或急或纵,其征象呈现睡眠与觉醒更替节律紊乱,或为瞋目不合,或瞑目不开,并伴随着心、脾、肝、肾及其相关经络的病证。
2.目标证候以顽固性失眠、手足烦热为主症;以口渴数饮、心烦卧起不安、大便灼肛、小便不利为次症。肝藏血,血分留热,肝气热,筋膜干而筋急而挛,故手足躁,不得安卧;肝脏浊气,逆而乘心,乱其神志,故心烦卧起不安;肝热必及于胃,胃热壅滞而失于和降,大便灼肛,小便不利,胃气不和则不得安卧;热邪在肝,故脉弦数有力;肾热则咽中干,口渴数饮;肾脉下抵足心,故足下热而欲覆冰冷却,热邪在肾,故脉沉而数。
第二节 肾气不充与中气不固是慢性失眠的基础病机
一、年龄差异和肾气不充是调节昼精夜寐节律的基础因素
【经文】
3.壮者之气血盛,其肌肉滑,气道通,营卫之行不失其常,故昼精而夜瞑。老 者之气血衰,其肌肉枯,气道涩,五脏之气相搏,其营气衰少而卫气内伐,故昼不精,夜不瞑。(《灵枢·营卫生会第十八》)
【注释】
①精:精力充沛(feel energetic)。
②不精:精力不足(be dispirited)。
③气道:宗气运行途径(pathways for original chest Qi to flow)。
④气血衰:神气不足(Qi and blood fall into decline,namely, spirit is debilitated)。
⑤肌肉滑:肌肉色泽光润(lubricious muscles)。
⑥肌肉枯:肌肉衰弱少色泽(emaciated muscles)。
⑦营气衰少而卫气内伐:气血亏虚(the nutrient Qi is deficient and the defense Qi is corrupted inside)。
【解读】
(一)气血盛衰和气道通涩是调节昼精夜寐自我适应节律的基础因素
气血盛衰、气道通涩具有调节自然睡眠、自然觉醒节律的基础作用,自然睡眠和自然觉醒的更替节律存在一定程度的个体差异。首先,机体筋骨强弱、气血盛衰存在固有的个体差异,《灵枢·通天第七十二》说:“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其态不同,其筋骨气血各有不同。”即使相同年龄、气平血和、气脉常通,其自然睡眠时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其次,年龄增长和性别因素所产生的气血盛衰亦源于不同的脏腑功能,《素问·上古天真论》指出,女性五七,阳明脉衰,男子五八,肾气衰,由于性别不同,其筋骨强弱、气血盛衰存在“七损八益”的规律。第三,自然睡眠时间取决于机体对环境的适应性和觉醒后精力充沛状态。机体年龄增长、脏腑功能减退、气血盛衰以及对环境适应性改变,其自然睡眠、自然觉醒自我适应节律亦会发生相应改变,经文指出自然睡眠时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缩短,虽然气血盛衰、气道通涩源于脾胃肾功能减退,但尚能维系自然睡眠和自然觉醒的自我适应节律。发生慢性失眠的关键因素是“五脏之气相搏,其营气衰少而卫气内伐”。经文中“壮者”与“老者”揭示气血的盛衰,无论壮与老,重要的机制是“气道通”,也就是《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所说的“气脉常通”!脾胃健运,气血生化有源;肾气充盈,气脉舒畅,如此则寤寐自然有序更替。《素问·方盛衰论篇第八十》说:“老从上,少从下”。森 立之注:“老年人脾肾自衰,心肺自盛者,以是为常,故曰从上。老人无病必宜如此。凡足弱膝冷便秘尿数,而耳目反聪明者,乃'从上’之义也。少者脾肾自盛,而心肺自衰者,以是为常,故曰'从下’。壮少无病必宜如此。凡饮食自倍,色欲满溢,思虑浅近,胸满喘咳者,乃'从下’之义也。”“五脏之气搏,营气衰少而卫气内伐”的临床结局是“精不化气,气不生精”!由此可知,尽管年龄增长因素的确会使夜间睡眠时间逐渐缩短,但并非所有人随着年龄增长都会发生慢性失眠,一方面反映机体对脾肾自衰所产生气血不足内环境自我调节的适应性,另一方面由于脾肾自衰所产生气血不足的内环境自我调节的适应性渐进性减退,机体出现眼花耳鸣,或手足清冷,或足弱膝冷,或便秘尿数征象,经文称这种现象为“五脏之气相搏,营气衰少而卫气内伐”。其临床结局表现为昼日神不清爽而夜卧不寐。可见,慢性失眠的性别、年龄分布特征为女性35岁以上,男性40岁以上。肾气不充,中气不固,五脏元真不得通畅,则肌肉枯、气道涩,五脏即不安和,五脏不和,营卫生始离合不循其常,则昼不精,夜不寐。
(二)肾气不充、中气不固是自然睡眠和自然觉醒自我适应节律失调的基础病机
首先,“胃不和卧不安”揭示脾胃不和、中气不固是发生“不得安卧”“卧不安”的主要病因,经文中“安卧”不完全是指睡眠,常常是指“懈怠安卧”。《素问·平人气象论篇第十八》说:“溺黄赤安卧者,黄疸”。《灵枢·论疾诊尺第七十四》说:“安卧,小便黄赤,脉小而涩者,不嗜食”。就睡眠状态而言,“安卧”的临床内涵是指虽形似睡眠,但不是处于睡眠状态。因而经文有“不得安”“有卧而有所不安”的明示。由此可知,“胃不和卧不安”与慢性失眠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但其并不具有特异性。
其次,经文所说的“肌肉滑”“肌肉枯”并非指肌肉之厚薄,而是指卫气行于腠理之通涩。《灵枢·本脏第四十七》说:“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合者也……卫气和则分肉解利,皮肤调柔,腠理致密。”张景岳说:“卫主气而在外,然也何尝无血,营主血而主内,然亦何尝无气。”张志聪注曰:“夫充肤热肉之血,乃中焦水谷之津液,随三焦出气,以温分肉,充皮肤。”《难经·六十六难》:“三焦之所行,气之所留止也……三焦者,原气之别使。”徐大椿撰《难经经释》注:“三焦者营卫之所出,营卫所留止之处,即三焦所留止之处也……三焦所在,即原气所在。”滑寿撰《难经本义》注:“三焦则为原气之别使,纪氏所谓下焦禀真元之气,即原气也。上达于中焦,中焦受水谷,精悍之气,化为营卫,荣卫之气,与真元之气通行,达于上焦也。”由此可知,三焦气化动力源于肾气,肾气不充则三焦气化不及而致营气衰少,卫气内伐。故仲景《金匮》说:“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腠者,是三焦通会元真之处,理者,是皮肤脏腑之文理”。中气不固,则致宗气虚乏而气道涩,故《灵枢·刺节真邪第七十五》说:“宗气不下,脉中之血,凝而留止。”又“脉者,血之腑”,且“心之合脉”,宗气不行,则神去气竭,故手足为之清冷。
第三,《灵枢·本神第八》“血脉营气精神,此五脏之所藏……脾藏营,营舍意,脾气虚则四肢不用,五脏不安……肾藏精,精舍志,肾气虚则厥,实则胀,五脏不安”。马莳注:“盖脾肾为胀,皆五脏不安,以胀则自不能安。”张志聪注:“肾为生气之源,故虚则手足厥冷,肾者,胃之关也,故实则关门不利而为胀。”《素问·调经论篇第六十二》说:“志意通,内连骨髓”。《 太素》注:“意是脾神,通于营气,志是肾神,通于三焦,原气之别使,皆以内连骨髓,成身形,及以五脏,故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由此可知,脾肾气虚皆可导致五脏不安,以致“魂魄飞扬,志意恍乱”,营气衰少,气乱于卫,三焦气化失调,津气同病和膜失柔和,并引起二蹻脉的纵缓、挛急而使得寤寐节律失调,呈现“目瞋不合”或“目闭不开”征象。慢性失眠的基础因素:①脾胃不和,气血两虚;②肾藏精功能下降。《素问·上古天真论》说:“气脉常通而肾气有余也”。肾阳强弱亦与气血通利与否有关。阳虚不能化气行水虽然属于津病,血运不利亦是引起肾功能障碍的因素之一。临床治疗重点在大补脾胃肾,协以调节气血盛衰、气道通涩则有助于改善入睡困难和恢复自然睡眠。值得注意的是,经文揭示出精生于谷,谷以养神的抗衰老方法,并指出脾、胃、肾功能状态常常影响营卫循行昼夜节律和寤寐更替!
【经验方】还少丹(《医学发明》)加减
熟 地黄30g 枸杞30g 生山药15g 山茱萸15g 茯苓12g 石菖蒲9g远志9g 续断15g 五味子12g 巴戟天15g 肉苁蓉15g 炒杜仲15g 怀牛膝15g 小茴香9g 麦冬15g
目标证候:入睡困难,甚至彻夜不眠,夜眠时间2~3小时,手足清冷,头胀痛,耳鸣眼花,肢体倦怠,腰膝酸困,小便浑浊。
(一)方解
《医学发明》载还少丹是一张调补虚损的好方子,东垣谓其功效曰:“大补心肾脾胃。治一切虚损,神志俱耗,筋力尽衰,腰脚沉重,肢体倦怠,血气羸乏,小便浑浊”。丁光迪教授说:“(还少丹)为肾气丸的变通方,即由肾气丸的补肾化气,变为温润之剂,煦濡水火。方中用巴戟天、苁蓉取代肾气丸中的附子、肉桂,是以温润之味,补肾气,滋精血,而无刚燥之嫌。杜仲、牛膝,可看作是巴戟天、苁蓉的重叠用药。孙真人云:'重复用药,药乃有力’。即是增强其补肝肾气血的作用。以五味子、枸杞易泽泻、牡丹皮,这又改通泄为守补,加重熟地黄、山药、山茱萸的滋养肝肾力量,正如东垣所谓'以味补肾真阴之虚’。从此看出,本方的重 点是使'阴本既固,阳气自生,化生精髓’者。配伍菖蒲、远志,能开心窍,益肾志,使心肾交通,水火既济,则神志可以通泰。特别肾为水火之脏,这种用药配伍,就更具有针对性和全面性。尤妙者,是用茴香一味,理气调中,开胃进食,配合茯苓,寓流通于诸补药之中,不仅守中有动,补而不滞,更重要的亦是健脾和胃,使精生于谷,谷以养神的方法;其能达到'大补心肾脾胃’之功是可以信赖的。总之,本方是颐养精气神的方法,所以名之曰'还少’,即还复'少火生气’之功,而使生化无穷。”
(二)临床应用
尽管临床采用益气健脾,养血安神,滋肾填精,益阴清火,交通心肾,镇静安神治疗中老年慢性失眠可短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继续治疗则慢性失眠并不能得到持续改善,甚至出现慢性失眠治疗无效,迄今为止,改善夜寐不安的临床效果远没有达到临床预期疗效。
慢性失眠自然病程中常常呈现心、脾胃、肾自衰的诸多外在临床征象,除了年龄差异、性别不同因素之外,中气不固、肾气不充则是构成慢性失眠病机的基本因素。一者肾藏精不足则肾气自衰,三焦津液转输出入功能减退,其腰膝酸困,耳鸣眼花,足软膝冷,小便浑浊表明肾阴阳两虚。二者脾胃自衰,生化营卫气血津液不足,其寐差多梦,肢体倦怠,手足清冷,头胀痛表明中气不固,逆气上冲而致宗气不下则神去气竭。病机呈现“五脏之气相搏,营卫衰少而卫气内伐”,病变脏腑关乎心脾胃肾,尤以肾气不足为显著。
老年慢性失眠者常见夜尿频、手足清冷或足胫冷,或因夜尿频而不得安卧,或入睡困难则夜尿频。《素问·厥论篇第四十五》说:“前阴者,宗筋之所聚,太阴阳明之所合也。春夏则阳气多而阴气少,秋冬则阴气盛而阳气衰。此人者质壮,以秋冬夺于所用。下气上争不能复,精气溢下,邪气因顺之而上也,气因于中,阳气衰,不能渗营其经络,阳气日损,阴气独在,故手足为之寒也。”滑寿撰《读素问钞·病能篇》注:“秋冬阴壮阳衰,人或时赖壮勇,纵情嗜欲于秋冬之时,则阳夺于内,阴气下溢,邪气上行,阳气既衰,真精又竭,阳不荣养,阴气独行,故手足寒,发为寒厥。”此上盛下衰的主要病因是“秋冬夺于所用”。由此可知,气化精生,味和形长是持续改善治疗中老年慢性失眠的有效方法。
二、脾胃气虚是卧而有所不安的基础因素
【经文】
4.人有卧而有所不安者……脏有所伤,及精有所之,寄则安,故人不能悬其病也。(《素问·病能论篇四十六》)
【注释】
①人有卧而有所不安:卧:睡眠(sleep calmly)。森立之:盖虚劳不足,似病非病,似不病非不病,唯是嗜卧而卧亦不安。
②精有所之,寄则安:《太素》作“精有所乏,倚则不安”。森立之注:是因于脏有所伤,及精有所乏,其卧亦倚侧不安,其状似不病,故他人不能见察其病。
③脏伤:脾胃功能失调(disorder of the spleen and stomach)。脏指脾胃。理由:倚侧不安则四肢倦怠,《灵枢·本神第八》:“脾气虚则四肢不用,五脏不安,实则腹胀泾溲不利”;《神农本草经》治疗脾胃的药物功效多次提及“五脏”。
④故人不能悬其病:太素作“故人不能泩悬其病”。森立之注:泩与省、醒等一音借字,泩悬即醒见。谓醒醒然见察其病。
【解读】
(一)嗜卧而卧不安是慢性失眠脾胃气虚证的临床征象
《素问·八正神明论》说:“养神者,必知形之肥瘦,营卫气血之盛衰,血气者,人之神”。神思清爽是气血调和的外在征象,营卫气血盛衰则是“精与神”生理活动的基础因素,同时,经文又强调“精、气、神”源于脾胃纳化、更虚更实的健全功能。《素问·五常政大论篇第七十》说:“阴精所奉其人寿,阳精所降其人夭。”《证治汇补》说:“奉者,脾胃和,谷气升,行春夏之令,故人寿;降者,脾胃不和,谷气下流,行秋冬之令,故人夭。升降之理,所关甚巨,所以脾虚久病,宜升阳扶胃药中,每寓升发之品。”然而,脾胃不和又有脾病、胃病之别,其临床征象亦不同。《脾胃论·脾胃胜衰论》说:“胃病则气短,精神少而生大热,有时而显火上行,独燎其面;脾病则怠惰嗜卧,四肢不收,大便泄泻。”故《素问·太阴阳明论篇第二十九》说:“太阴阳明为表里,脾胃脉也,生病而异者何也?阴阳异位,更虚更实,更逆更顺,或从内,或从外,所从不同,故病异名。”但经文又强调脾胃不和病证的临床转归重在胃气强弱。如《素问·玉机真脏论》以五脉太过、不及起,以五脏虚实收,中间论外淫,论内伤,而推极于真脏,总是归重胃气。胃气不和与“卧而有所不安”密切相关。《素问·逆调论》说:“胃不和则卧不安”。张景岳注:“不安,反覆不宁之谓”。《素问·评热病论》说:“不能正偃者,胃气不和也。”高世栻注:“正偃,安卧也。胃不和卧不安,即此阳明逆不得从其道之谓”。脾胃气虚,营卫未和,营血不足,卫气独行于阳,不得入于阴,故昼间昏昏欲睡,夜间兴奋难以入睡,心烦不得卧,起后又倦怠,乏力,嗜卧,晨起后精神不爽,头脑昏沉。此外,慢性失眠还有一种现象,除了夜寐不安,或似睡非睡,或夜寐时间短,或夜寐易醒,醒后难以再入睡之外别无所苦,这类夜寐不安的现象即是经文所说“有卧而有所不安”,“人不能泩悬其病”而呈现“神脏(spiritual viscera)”有所伤的临床征象。值得一提的是,脾为胃行其津液,津液相成亦为神安其舍的必要条件,《素问·六节脏象论篇第九》说:“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脏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王冰注:“五气和化,津液方生,津液与气,相副化成,神气乃能生而宣化也。”脾胃气虚,津液不行则留为痰饮,津停气阻,少阳三焦与胆疏泄不利,则形成津气同病和膜失柔和,并引起二蹻脉的纵缓、挛急,呈现“目瞋不合”或“目闭不开”征象。顺气化痰治疗痰涎沃心而致心气不足的不眠;清痰抑火治疗火炽痰郁而致不眠皆是对“津液相成,神乃自生”的临床注解。
(二)慢性失眠脾胃气虚迁延日久可呈现精血虚乏病证
胃气不和所致“目瞋不合”;脾虚湿阻所致“目闭不开”皆为脾胃气虚的主要病证。《素问·玉机真脏论》:“五脏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本”。《素问·脉要精微论篇》从脉象更证实了胃气盛是“五脏者,身之强也”的基础因素。经文论述五脏虚实病证时强调“脾气虚则四肢不用,五脏不安。”胃气不和,上下不得其气,五脏不安。《素问·六节脏象论》说:“肾主蛰,脏之本,精之处也。”《灵枢·本神第八》说:“肾气虚则厥,实则胀,五脏不安。”由此可知,脾病、胃病、肾病均出现“五脏不安”的病证,而经文又称五脏为“五神脏”,脾胃纳运升降,肾藏精而血脉通畅,如此则如《灵枢·平人绝谷》所说“气得上下,五脏安定,血脉和利,精神乃居”。故寤寐节律隶属于五神脏功能活动外在征象。有理由认为,脾胃气虚、肾不藏精是构成慢性失眠脏腑虚实病证转化的基础因素。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精食气,形归味”。又说:“精化为气,气伤于味”。
“卧而有所不安”多见于大病后,脾胃虚弱,气血两虚,营卫未和,卫气独行于阳而不得入于阴,其临床征象为虚羸少气,身重,体倦怠惰,足膝无力,夜间虽卧而似睡非睡,时醒时睡,晨起则头昏沉,神不清爽,通常给予人参养荣汤将息调理,待气血复,营卫和亦可取得昼精而夜寐的疗效。然而,慢性失眠更常见到的“卧而有所不安”征象仅为虚烦不寐,或即使能够入睡,但睡眠时间不足,迁延日久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走神,记忆力减退,手足不温,治疗初期以归脾丸可以有效改善虚烦不寐或睡眠时间不足。由于虚烦不寐或睡眠时间不足经常反复发生,长期使用归脾丸化裁治疗慢性失眠,其改善失眠的效果却逐渐下降,若早晨服归脾丸,夜间临睡前给予六味地黄丸,在虚烦不寐持续得到改善的同时,记忆力也有所恢复,且神思清爽,手足温和。符合经文“脏有所伤,精有所乏,倚则不安”所揭示由脾胃气虚、肾精虚乏而致慢性失眠的发病机制。又《素问·调经论篇第六十二》说:“志意通,内连骨髓”。脾胃气虚,则肾精无以气血滋养,张景岳称:“五脏久病,穷必及肾”。《脾胃论·脾胃胜衰论》说:“大抵脾胃虚损,阳气不能生长,是春夏之令不行,五脏之气不生。脾病则下流乘肾,土克水则骨乏无力,是为骨痿。令人骨髓空虚,足不能履地,是阴气重叠,此阴盛阳虚之证。”有鉴于此,慢性失眠脾胃气虚证日久不愈,则可继发肾精虚乏、髓海空虚而发为骨痿,其临床征象《素问·痿论》说:“肾气热,则腰脊不举,骨枯而髓减,发为骨痿”。又《灵枢·海论》所说:“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酸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因此,在补气健脾、和胃生津的同时兼以益肾法是改善和提高慢性失眠临床疗效的有效途径。
(三)卧而有所不安是气虚郁滞的主要临床征象
卧而有所不安源于两个方面:一者气血不足,神思不爽,卧而不睡,所谓“脾气虚则四肢不用,五脏不安”以致“魂魄飞扬,志意恍乱”,“五脏之气相搏,营气衰少而卫气内伐”,故昼不精而夜不寐;二者津液不行,湿阻气滞,气不得上下,五脏不安,所谓“津液相成,神乃自生”。换言之,气、血、津、液是维系五神脏生理活动的物质基础,五脏安定则神乃自生,精神乃居。由此可知,气、血、津、液的盈虚盛衰皆关乎脾胃纳运升降运动是否正常。脾胃功能主要体现在升清降浊两个方面。脾的运化作用表现在藏而不泻,喜通恶滞,喜升恶陷,以健运升通为顺的生理特点。故《素问·经脉别论篇第二十一》说:“食气入胃,浊气归心。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脾主运化,水谷精微通过脾的运化和转输作用,上输到心肺等脏生化为气血津液。胃肠的虚实更替,表现在泻而不藏,动而不静,降而不升,实而不能满,以通降为顺的生理特点。故《灵枢·平人绝谷第三十二》说“胃满则肠虚,肠满则胃虚,更虚更满,故气得上下,五脏安定。”胃纳脾运,胃降脾升,纳运相得,升降相因成为一体。脾胃纳运功能所反映的升降两种基本运动形式,也就成为脾胃的生理特征。显然,脾胃气虚则脾胃纳运功能所反映的升降基本运动形式出现异常,气虚郁滞成为脾胃气虚的主要特征。胃气不和则气不得上下而五脏不安,脾气虚则四肢不用而五脏不安,故卧而有所不安是脾胃纳运升降功能异常,脾胃气虚既可呈现气血不足的证候,又可出现津液不行、留而为湿或为痰饮的病证。由此可知,慢性失眠脾胃气虚征象多表现为气虚郁滞的特点。因此,李东垣提出“安养心神调治脾胃”的治疗思路。
【经验方】益气安神汤
黄芪20g 升麻6g 太子参15g 苍术12g 生白术12g 砂仁6g 当归6g生姜6g 青皮6g 橘皮6g 炙甘草6g 黄柏6g 麦冬12g 五味子12g 炒神曲9g
目标证候:长期夜间睡眠时间不足,或寐差,神思不安,舌淡红,舌苔薄白根垢,右脉浮大而数,左尺沉。
(一)方解
此方是依据李东垣创制的黄芪人参汤化裁而成。黄芪、太子参、生白术、炙甘草、升麻甘温益气升阳以鼓舞脾胃;黄芪、当归益气补血;太子参、麦冬、五味子益气生脉,复其心主血脉,肺主治节;苍术、陈皮、青皮、砂仁芳香之味,理气、燥湿,醒脾以解郁滞;《玉楸药解》说:“白术入胃,其性静专,故长于守,苍术入脾,其性动荡,故长于行,入胃则兼达辛金而降浊,入脾则并走乙木而达郁。白术之止渴生津者,土燥而金清也,苍术之除酸而去腐者,土燥木荣也。若是脾胃双医,则宜苍术、白术并用。”佐以生姜、神曲健脾和胃。《本经》称黄柏“主五脏肠胃中结热”。杨时泰撰《本草述钩元》说:“盖热之结者,胃阳不得化,肾阴达于胃,而胃阳化矣。”《长沙药解》说:“黄柏苦寒迅利,疏肝脾而泻湿热,清膀胱而排瘀浊,殊有捷效。”李东垣称黄柏与黄芪合用“使足膝之力涌出”,称黄柏与苍术合用可“俾下焦湿热散行”。黄柏、砂仁、炙甘草又称封髓丹,陈修园说:“(黄柏)以其苦寒坚肾,佐以甘草以缓泻肝火,使水土合为一家。尤妙于砂仁为引导,即《内经》'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义也。”诸味合用共奏益气健脾以复脾胃纳运升降之功。
(二)临床应用
舌象、脉象是主要应用指征。经文说:“脏有所伤,及精有所乏,倚则不安”为“人卧而有所不安”病证的主要病机。因此,卧而有所不安是昼不精而夜不寐的证候之一。经文在不同篇章中反复强调脾、胃、肾各自盛衰皆与五脏是否安定密切相关,只有脾胃纳运升降、肾藏精气化皆不失其常,则“五脏安定,血脉和利、神乃自生”。由于“脏有所伤,及精有所乏”,故卧而有所不安的主要病机为脾胃气虚。脾胃气虚,清阳不升,则心不主血脉,肺不主治节;浊气不降,则水湿不得运化,湿阻气滞,中气沉降而内生下焦湿热,故气虚郁滞是此类病证的基本特征。治疗以益气健脾复其脾胃纳运升降是取得慢性失眠疗效的关键措施。李东垣撰《脾胃论》说:“善治斯疾者,惟在调治脾胃,使心无凝滞,或生欢欣,或逢喜事,或天气暄和,居温和之处,或眼前见欲爱事,则慧然如无病矣,盖胃中元气得舒伸也。”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脾胃气虚、纳运升降失调是病机的关键所在,虽有下焦湿热,但不宜淡渗分利克伐脾气,虽营血虚乏,但亦不宜浪投滋阴补血而徒增壅滞。故张景岳撰《景岳全书·不寐》说:“凡人以劳倦思虑太过者,必致血液耗亡,神魂无主,所以不寐。既有微痰微火者不必顾,只宜培养气血,血气复则诸证自退。若兼顾而杂治之,则十曝一寒,病必不愈。”
第三节 气血逆乱是寤寐节律紊乱的基本特征
一、气血逆乱是外邪逆于脏腑的基础因素
【经文】
5.夫邪气客于人也,或令人目不瞑,不卧出者,何气使然?……今厥气客于五脏六腑,则卫气独卫其外,行于阳,不得入于阴。行于阳则阳气盛,阳气盛则阳蹻陷,不得入于阴,阴虚,故目不瞑。(《灵枢·邪客第七十一》)
【注释】
①不卧出者:《甲乙经》“或令人目不瞑,不卧出”作“或令人目不得眠者”。钱熙祚说:“原刻'卧’下衍'出’字,依《甲乙经》删”。但经文谈到有“不得卧”“不得安卧”,没有“不卧”句法。周学海疑“不卧出者”为“不汗出者”(no perspiration)。经文有“不得卧”“夜不寐”“目瞋”“不得正偃”等均归因于胃气不和。《甲乙经》作“邪气客于人,或令人目不得眠者”亦没有提及表证。因为上文有“邪气客于人”,则“不卧出”作“不汗出”,则明确指出厥气客于五脏六腑所致“目不瞑”是没有表证的。因此,周学海疑“不卧出”为“不汗出”符合经文原义,“不汗出”与无表证互文见义。
②邪气:外邪(exogenous evil)。
③厥气:《太素》注:“厥气,邪气也。”即外邪(exogenous pathogenic factors)。
④阳气盛:《太素》注:“阳气瞋”(the defense Qi is inordinate)。
⑤阳蹻陷:陷:满(stagnation)。卫气独行于阳,不得入于阴,阳气盛则阳蹻满。
⑥阴虚:营气虚(debilitating nutrient Qi)。
【解读】
(一)胃气不和是邪气逆于内所致卫气功能失常的始动因素
“目不瞑”属于“邪气客于人”的独立的临床病证,并非是其或然病症。无论“邪气”或是“厥气”,经文重复使用“客”字,表明此邪气属于外邪内逆而不是内生邪气。如果是外感六淫邪气,那么卫气病证是当然病证或所生病证有表证征象,但经文并没有首先谈到卫气病证或表证,却指明是“厥气客于五脏六腑”,由于邪气逆于内,继之出现卫气功能失常,进而呈现“目不瞑”征象。换言之,卫气独行于外,行于阳,不得入于阴的病因是由于邪气内逆于五脏六腑,进而表明“目不瞑”征象与营卫不和病机存在关联性。仲景《伤寒论》关于营卫不和病证的阐述是有表里之别的,在表有桂枝汤证,在内有小建中汤证。“目不瞑”仅仅是作为或然症存在于六淫所致营卫不和病证中。又《诸病源候论·虚劳病诸候·大病后不得眠候》说:“大病之后,脏腑尚虚,营卫未和,故生于冷热。阴气虚,卫气独行于阳,不入于阴,故不得眠。若心烦不得眠者,心热也;若但虚烦而不得眠者,胆冷也。”显然,“目不瞑”作为或然症存在于这些病证中,与经文所说的“邪气客于人”“厥气客于五脏六腑”所说的“目不瞑”病证不同。由于营卫之气出于中焦脾胃,且“目不瞑”征象与营卫不和病机的关联性,由此可知,经文所说的“邪气”“厥气”皆归因于胃气不和而致“目不瞑”病证!由于经文并没有谈到“目不瞑”伴随相关的脾胃纳运升降失调病证,所以,此处胃气不和并不是指胃肠疾病,仲景说“胃气因和,津液得下”,《灵枢·平人绝谷第三十二》说:“神者,水谷之精气也。”又《素问·六节脏象论》说:“津液相成,神乃自生”。《素问·评热病论篇第三十三》说:“人之所以汗出者,皆生于谷,谷生于精……汗者,精气也。”有理由认为,经文中“不汗出”揭示胃气不和源于脾胃功能失调病机。由于卫气独行其外,行于阳,且卫气之行或迟或速,奇经八脉调节气血渗溢失常而出现二蹻脉“沟陷渠沮”,从而引起睡眠与觉醒更替节律紊乱而出现瞋目不合与瞑目不开征象。故经文说“阳气盛,则阳蹻满”。其次,胆、三焦和膀胱参与调节津液气化转输出入皆与阳蹻脉渗灌疏泄相关,因此阳蹻脉渗灌调节功能异常,则“目不瞑”多伴随气机升降失调和气血津液出入紊乱的临床征象。
(二)“厥气客于五脏六腑”探析
《灵枢·邪客》篇中谈到邪客所引起的疾病有目不得眠、不得视及多卧、卧不安、不得仰卧、肉苛和诸息有音而喘。这些病证彼此独立,各证病机有所不同,这亦证实“邪气”所致病证属于杂病范畴。此条经文从邪气客于五脏六腑,与仲景《伤寒论》邪气客于三阴三阳所致六经病证有所不同。故此邪气与正邪实风不同,“厥气”理应属于虚邪贼风。首先,虚邪贼风是通过腠理开闭而致病,腠理开闭是感虚邪贼风所致病证深浅的原因,因虚邪贼风客于皮肤腠理,如《灵枢·岁露论第七十九》说:“贼风邪气之中人也,不得以时,然必因其开也,其入深,其内极病,其病人也猝暴;因其闭也,其入浅以留,其病也徐以迟。”故经文以“卫气独卫其外”自训“客”字揭示脏腑所受之邪属于虚邪贼风。其次,感虚邪贼风而致病的机制,《灵枢·贼风第五十八》说:“此亦有故邪留而未发,因而志有所恶,及有所慕,血气内乱,两气相搏,其所从来者微,视之不见,听而不闻。”第三,虚邪贼风性质属阳,或入腑、或入脏,《素问·太阴阳明论篇第二十九》说:“犯贼风虚邪者,阳受之,食饮不节,起居不适者,阴受之。阳受之则入六腑,阴受之则入五脏。入六腑,则身热,不时卧,上为喘呼。入五脏则䐜满闭塞,下为飧泄,久为肠澼。”张琦撰《素问释义》注:“腑阳脏阴,各从其类。按《阴阳应象大论》云:“天之邪气感则害人五脏,水谷之寒热感则害人六腑。”与此正相反而又实相成。以形气言,邪气无形故入脏,水谷有形故入腑。以表里言,腑阳主外故贼风虚邪从外而受,脏阴主内故食饮不节从内而受。实则腑脏皆当有之,盖内外之邪,病情万变,非一端可尽,故以广陈其义耳。”第四,经文阐述邪气致病,以虚邪贼风与水谷寒热并举,所致病证皆为邪气伤脏腑,或腠理,或形体,或三焦。《金匮·脏腑经络先后病》说:“客气邪风,中人多死。若能养慎……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不遗,形体有衰,病则无由入其腠理。”仲景亦强调人不能养慎包括虚邪贼风,饮食不节和起居不适,其病证为脏腑,或为形体,或为腠理,或为三焦。第五,虚邪贼风病源复杂,病证各异,证亦独立,病有定所,自可从症状论治。“邪气客于人”所致“目不瞑”病证源于营气虚乏。《素问·痹论第四十三》说:“营者,水谷之精气,和调于五脏,洒陈于六腑,乃能入于脉也。”此“厥气客于五脏六腑”是指营气病变,故经文说“阴虚,故目不瞑”。
(三)卫气失常兼以营气虚乏和气滞津凝是“目不瞑”病证的病机特征
“目不瞑”是虚邪贼风所致的独立病证。其始动因素源于不能“养慎”,以饮食不节、起居不适导致脾胃功能失调是主要病因。其次,血气内乱,营卫失和是“厥气客于五脏六腑”的基本特征。经文强调营气虚是“目不瞑”病证的主要病机,《素问·痹论第四十三》说:“阴气者,静则神藏,躁则消亡”,营气虚乏,神不守位则为“目不瞑”。同篇经文指出营气虚源于胃气不和而水谷不化精微。由于饮食不节和起居不适引起失眠等疾病已经为多数人们生活实践反复证实。关于血脉与三焦是营卫环流之路,陈潮祖教授在《中医治法与方剂》说“营卫之中气血各行其道,均有津液、谷精、肾精相随,运行全身,成为脏腑功能活动的能源。营卫所行清气,是从肺系气道间隙进入血络;水谷精液,是从脾系肠道间隙进入血络;肾系之精是从命门系膜进入血络。由于均有部分气、血、津、液、精未曾进入心系,在其少阳三焦运行,因此血脉内外,环流物质基本相同,唯有血液是从骨内血络进入脉内,不行脉外而已。气血津液精中,清气称为阳气,血津液精称为阴精。简称阴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由于血津液精虚乏,清气不得顾护其外,“卫气独卫其外,不得入于阴”“阳气盛”。《灵枢·五癃津液别》说:“三焦出气,以温分肉,充皮肤,为其津,其留而不行者为液”。显然,除卫气病变之外,尚兼有营气、津气病变。由此可知,胃气不和、营卫不谐协、气滞津凝、血气内乱构成“目不瞑”的病机特点,临床征象为虚烦,卧而有所不安,目不瞑。
【经验方】高枕无忧散
太子参15g 生石膏15g 陈皮12g 姜半夏12g 白茯苓12g 枳实12g竹茹9g 川芎6g 炙甘草9g 炒酸枣仁15g
目标证候:头脑昏沉,烦躁不得安,不得眠,能食而倦怠乏力,舌红苔薄白,脉浮数。
(一)方解
经文指出“目不瞑”的治疗方法为“补其不足,泻其有余,调其虚实,以通其道,而去其邪”,目标疗效为“决渎壅塞,经络大通,阴阳得和”。高枕无忧散药物配伍突出在燮理胃气不和、清解膈间虚热!和中清热:生石膏,炙甘草;通脾胃大络:太子参,竹茹;通调津液:半夏,茯苓;利胸膈:陈皮,枳实。此为“决渎壅塞,经络大通”而立。酸枣仁泻肝郁而润风木,滋生脾液,以上养心液,下益水精,使精液生,风燥泻,营血流,阳气归,瘀着自失其根。故《本经》曰:“主心腹寒热,邪结气聚,四肢酸疼湿痹……安五脏”。与山茱萸功效相似!《本经》并没有提及酸枣仁治疗失眠,酸枣仁治疗失眠源于《金匮》,这也支持不能完全用《本经》药效解释经方药效的结论。处方中确实融入酸枣仁汤,但经方原文中的“虚劳”,并非气血津液和五脏六腑疲敝所导致的虚劳病。实际是指心烦,不得眠,特征是“食[插图]”(虽能食,但疲劳倦怠感显著)。若为真正的虚劳应当食欲减退。此方以陈皮、枳实、竹茹、石膏、川芎通经络泻其实,佐以太子参、茯苓、甘草补其虚,以半夏燮理阴阳,故全方通补结合达到阴阳得和的目标疗效。以此证甚多,高枕无忧散对于彻夜不眠、心悸疗效甚好!
(二)临床应用
贼风虚邪和腠理开闭是营卫失和所致“目不瞑”的始动因素,由水谷寒热之邪所致胃气不和、中气不固是营卫失和的基础病机。经文突出“目不瞑”病证的病机在营卫之行环流障碍。由于气血津液化生源于脾升胃纳,胃气不和,胃肠虚实更替失调,气不得上下,五脏不安,脾不升清则倦怠乏力,精微匮乏,纳谷倍增,而胃气日损。故中气伤则精损、气乏、神不足,寤寐昼夜调节亦因之而失调,病变过程兼以并发三焦病变,因三焦乃营卫之行环流之路,营卫失和亦揭示三焦病变呈现津气筋膜的综合病变征象。经文所揭示的失眠的临床症状表述如下:①由于阳气盛,阴气虚临床表现出能食而倦怠乏力,心悸、烦躁不安或焦虑等情绪躁动不安;②二蹻脉功能失常的临床表现为“目不瞑”“不得卧”伴随肢体功能拘挛或缓纵;③津液气化失调则临床表现为小便频数、面目虚浮若肿和头脑昏沉。“目不瞑”病机还有一个环节即“(卫气)行于阳则阳气盛,阳气盛则阳蹻满”,揭示阳蹻脉渗灌调节气血津液障碍,出现津、气、血阻滞而表现为“阳蹻满”之“目瞋”的征象。由于胃气不和,中气不固,则宗气不足,经文所说“卫气独卫其外,行于阳”揭示宗气不得下,血行不畅导致胸膈气机不利,故呈现烦躁不得卧的临床征象。
二、肾气阴两虚加重或促使寤寐节律自我调节功能失常
【经文】
6.病 而不得卧者,何气使然?……卫气不得入于阴,常留于阳,留于阳则阳气满,阳气满则阳蹻盛,不得入于阴则阴气虚,故目不瞑矣。(《灵枢·大惑论八十》)
【注释】
①阳气满:卫气有余(defense Qi tending to be excessive)。
②阴气虚:肾气阴两虚(nutrient Qi tending to be deficiency)。
【解读】
(一)卫气之行失常和阳蹻脉渗溢气血功能失调
经文反复申明“阳蹻盛”在“目不瞑”发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指出“阳气盛”与“阳蹻满”的因果关系。《难经·二十八难》指出奇经八脉具有“沟渠满溢,流于深湖……人脉隆盛,入于八脉,而不环周”的疏浚调节功能。由于卫气之行或迟或速而不得循其常,气乱于卫,卫气不与营气谐协则营卫失和,奇经八脉因“沟陷渠沮”,致使其渗溢气血的调节功能障碍,二蹻脉交通阻滞,导致三阴、三阳经络气血津液逆乱,故呈现“卫气不得入于阴,常留于阳”而致“阳气满则阳蹻盛”。诚如张景岳所说:“凡人之寤寐,由于卫气。”经文指出卫气常留于阳,阳气盛而阳蹻满,阴气虚是形成“目不瞑”的主要病机。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尽管外感六淫,或饮食不节、起居不适,或七情所伤均可呈现卫气病变征象,如温病中的三焦病证、卫气营血病证以及杂病中脏腑经络先后病证,即使奇经八脉出现病证征象,如妇科杂病中因冲、任、督、带失调而致的病证,这些病证并非均是以寤寐节律紊乱为主要病机的病证,即使“目不瞑”作为这些病证中的或然症,那么相同的病证亦并非均出现睡眠障碍征象。如何理解这些临床现象呢?《灵枢·禁服第四十八》说:“卫气为百病母”,揭示卫气病变或源于虚邪贼风,或源于脏腑太过不及,换言之,引起卫气病变的病因是多元的,虽然卫气病变不是睡眠障碍的特异性病因病机,但卫气病变是潜在睡眠障碍的病机。这一结论源于《内经》在不同篇章阐述“目瞋不合”“目闭不开”的病机。尽管不同杂病的病机和病证征象不同,但由于卫气病变,则其出现有的以睡眠障碍为主要病证,有的以睡眠障碍为或然症的临床现象。如此条经文“病”字是指内因所致独立的疾病,“不得卧”“目不瞑”则为其或然临床征象,这可以从同篇经文:“治此诸邪奈何?先治其脏腑,诛其小过,后调其气,盛者泻之,虚者补之,必先明知其形志苦乐,定乃取之”可以得到证实。在治疗“目不瞑”病证时,经文强调明了机体的形志乐苦是确定调治脏腑功能太过不及措施的首要前提。《素问·血气形志篇第二十四》说:“形乐志苦,病生于脉……形乐志乐,病生于肉……形苦志乐,病生于筋……形苦志苦,病生于咽嗌(《新校正》云:按《甲乙经》“咽嗌”作“困竭”)……形数惊恐,经络不通,病生于不仁。”形志乐苦伤于脉、筋、肉、精、血有形之质,病因皆如《素问·经脉别论》所说:“生病起于过用”,其病机如《灵枢·口问》所说:“血气分离,阴阳破散,经络厥绝,脉道不通,阴阳相逆,卫气稽留,经脉空虚,血气不次,乃失其常”。由此可知,形志乐苦所生病证皆为失于“养慎”!这些病证病机的共同特征如《素问·调经论》所说:“五脏皆出于经隧,血气不和,变化而生百病。”血气不和,其盛衰逆顺皆损伤脾胃之气。清·王燕昌撰《王氏医存校注》说:“然所由为病,乃在中气,动胜静,则真阴不足,其病皆阴虚火盛;静胜动,则真阳不足,其病皆阳虚火弱;动静俱衰,则真元亏损;动静俱盛,则诸病不生。”
有鉴于此,脏腑功能太过不及,继发卫气病变而致二蹻脉渗溢气血失调是发生“目不瞑”病证的症结所在,由于脾运胃纳升降、肾藏化功能太过不及均有“五脏不安”的病证并伴随卫气病证,所以,“目不瞑”病证与胃气不和密切相关,病程迁延可并发肾藏化功能异常的病证。
(二)肾气阴两虚加重或促使寤寐节律自我调节功能失调
《素问·痹论第四十三》说:“卫者,水谷之悍气也,其气慓疾滑利,不能入于脉也,故循皮肤之中,分肉之间,熏于肓膜,散于胸腹。”张景岳注:“凡腔膜肉理之间,上下空隙之处,皆谓之肓。膜,筋膜也。”表明“肓膜”与陈潮祖教授所说的“三焦由膜腠组成,是津气运行之路”互文见义。《灵枢·邪客第七十一》说:“卫气者,出其悍气之慓疾,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肤之间而不休者也。昼行于阳,夜行于阴,常从足少阴之分间,行于五脏六腑。”《灵枢·卫气行第七十六》说:“卫气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于身,昼日行于阳二十五周,夜行于阴二十五周,周于五脏……阳尽于阴,阴受气矣,其始入于阴,常从足少阴注于肾……是故人之所以卧起之时有早晏者,奇分不尽故也。”张景岳说:“所谓奇分者,言气有过度不尽也。”卫气行于表里,在表行于四末分肉皮肤之间不休,在里散于胸腹,行于五脏六腑。卧起之时有早晏不同,起因于卫气行于阴阳,有过度和不尽之分。卫气行于阴阳的分别之处为肾足少阴之分间。阴蹻脉亦起于肾足少阴经,在目内眦合于足太阳经和阳蹻脉。肾气盛衰及肾阴盈虚与阴蹻脉渗灌津液精血的调节功能密切相关,若肾气阴两虚而脉有所结,则可致阴蹻脉陷。阳蹻脉起于足太阳经,交于风池,在目内眦合于阴蹻脉。阴蹻陷,阳蹻满皆为二蹻脉渗溢气血津液的交通功能障碍,致使“沟陷渠沮,津血不得入于深湖”,形成阳不入阴,阴不出阳的病机。由此可知,肾藏化功能失常则可呈现卫气病变,阴蹻脉陷,则脉络瘀阻,营血郁滞;阳蹻脉满则三焦气化不利和津气转输出入失调的病证。故《灵枢·根结第五》说:“少阴为枢,枢折则脉有所结而(下焦水道)不通”!肾气不充,卫气虚乏,蓄积不行,苑蕴不得其常所,则津液不行而为痰饮病证。如《灵枢·卫气失常第五十九》说:“卫气留于腹中,蓄积不行,苑蕴不得常所,使人支胁(悬饮)胃中满(痰饮),喘呼逆息(支饮、溢饮)”。仲景称其卫气不足引起津液潴留的病证统称为痰饮病证。从此条经文说“阳气满则阳蹻盛”可知,此“目不瞑”由于阳蹻脉渗溢气血津液障碍导致卫气有余而不得行其常所,其病证有津气阻滞和营血郁滞的征象,可见头脑昏沉,胸膈烦热,烦躁不得卧,夜眠易醒,健忘,胃脘痞满,舌质暗红,苔薄白腻。故经文说:“卫气常留于阳”。由于肾气阴不足而脉络瘀阻,致使阴蹻脉陷,而令阳气不得入阴,故经文说“不得入于阴则阴气虚”。此“阴气虚”揭示肾气阴两虚加重或促进寤寐节律自我调节功能失调。此条经文的“阳气满”“阴虚”与第5条经文的“阳气盛”“阴气虚”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目不瞑”属于杂病中的或然症。此条经文强调内因引起卫气常留于阳,不得入于阴,阳气满而阳蹻脉盛,揭示卫气有余而不得行其常所而形成的津气阻滞和营血郁滞,阴气虚所致“目不瞑”表明肾气阴两虚则加重或促进“目不瞑”。
【经验方】薯蓣丸(《备急千金要方》)
黄芩12g 白芍15g 生地15g 竹叶9g 前胡12g 生甘草9g 生山药20g太子参20g 麦冬15g 远志9g 茯神12g 枳实9g 薏苡仁20g 姜半夏9g茯苓15g 生姜9g
目标证候:入睡困难,夜眠易醒,醒后难以入睡,头脑昏沉,胸膈烦热,胃脘痞满,食欲不振,大便不畅。舌质暗红,苔薄白腻,脉弦。
(一)方解
从薯蓣丸治疗慢性失眠临床实践分析药物配伍:经文反复强调阴气虚是发生“目不瞑”的重要病机,以生山药、太子参、麦冬、生地、白芍、远志、茯神养血安神;矢数道明撰《汉方临床处方解说》中认为黄芩、白芍合用具有“通血痹”的作用,我们使用黄芩、白芍配伍治疗慢性肾炎和复杂性尿路感染湿热证时证实其“通血痹”功效。《本经》称生地亦具有“通血痹”功效。生地增加胃中津液,补全身之阴,补血中之津液从而使血流改善起到通血络作用。以黄芩、白芍、生地协同增效,增强疏经通络;由于胃气不和,中气不枢,宗气不得下,心气凝滞,血行不畅而胸膈气机不利,经文称为“卫气常留于阳,而不得入于阴。”故以枳实、前胡、半夏、茯苓、生姜、薏苡仁散中焦结实,去胃中痰浊,而胃气得和;以黄芩、竹叶、前胡、生甘草除胸中烦热。
(二)临床应用
此证以慢性失眠、头脑昏沉为主诉,但以胃脘痞满、大便不畅为宿疾,以入睡困难、夜寐易醒、醒后难以入睡、胸膈烦热为新疾。此类证候多见于50岁以上男性,间歇性出现心悸,胸闷塞不适。心电图检查发现窦性心律,ST段低平。胃镜和肠镜检查均没有发现异常。每晚服药,用药5天内的证候变化一般首先出现肠鸣,矢气频,随之胃脘痞满消失,继之酣睡,晨起后即解大便,大便畅快,便后腹中舒适。昼间长期头脑昏沉,胸膈烦热完全消失。服药后的证候变化及其治疗效果,与《灵枢·平人绝谷第三十二》所说“胃满则肠虚,肠满则胃虚,更虚更满,故气得上下,五脏安定”基本相同,李东垣称为“胃中元气得舒伸也”。
内伤杂病主诉慢性失眠是临床经常遇到的问题,例如免疫性甲状腺疾病气滞血瘀证主诉以寐差多梦,代谢综合征合并慢性心肾损害湿热血瘀证亦常伴随睡眠障碍,卵巢早衰、围绝经期性激素失调冲任失调证主诉慢性失眠等。理想的治疗效果是内伤杂病证候得到改善的同时睡眠障碍亦随之改善,但更常见的临床现象是,若睡眠障碍得不到有效治疗,内伤杂病也难获得疗效,相反慢性失眠会加重或促进内伤杂病的发生发展,呈现内伤杂病的缓急轻重与睡眠障碍相互影响的临床现象。此条经文阐述了内伤杂病伴随慢性失眠的病因病机,并为处理内伤杂病主诉慢性失眠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此类问题的思路。
《灵枢·邪客》强调“目不瞑”的治疗方法为“决渎壅塞,经络大通”,提示由虚邪贼风所致血气不和,气血逆乱导致的寤寐节律自我调节功能失常,治疗的重心在祛除致病因素,辅以调其气血。《灵枢·大惑论》给出治疗“目不瞑”的方法是“先治其脏腑,诛其小过,后调其气,盛者泻之,虚者补之。”提示内伤杂病由脏腑功能失调所致的血气不和,气血逆乱导致寤寐节律紊乱,治疗的重心先脏腑病证,盛者泻之,虚则补之,依据脏腑气血虚实证候的标本缓急而“诛其小过”,后调其气血。二者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目不瞑”的病机皆为“阳气盛则阳蹻脉满,(卫气)不得入于阴而阴气虚”。半夏秫米汤使用秫米益气和胃,揭示调其气血治疗“目不瞑”的核心为和胃气,甘温益气、养阴生津、益气养阴、行气和胃、健脾养胃等是治疗慢性失眠的重要治法。可见“诛其小过”与“决渎壅塞”异文义同。经文称半夏秫米汤疗效机制为“阴阳得和”,同样亦适宜于杂病而不得卧的疗效机制,所不同的是调其气血方面,内伤杂病而不得卧须先治脏腑阴阳虚实而后调其气血津液。经文中强调“阳气盛”“阴气虚”是脏腑阴阳虚实病机,提示育阴生精,养血安神是主要的治疗措施。由于肾气阴两虚加重或促进寤寐节律自我调节失调,因此育阴生精,养血安神的重心在固肾气,益肾阴。《灵枢·根结》说:“少阴为枢,枢折则脉有所结而不通”,表明益肾阴须兼顾通经络之法,即经文所说的“决渎壅塞,经络大通”。临床已证实,杂病治疗效果与中气是否旺盛密切相关,对于证候复杂多变甚至危重证候,治法始终以顾护中气温凉动静是取得疗效的王者之道,可知“诛其小过”贵在顾护胃气。
三、胆气疏泄不利加重慢性失眠津气阻滞证发生发展
【经文】
7.因于寒,欲如运枢,起居如惊,神气乃浮。(《素问·生气通天论第三》)
【注释】
①寒:寒气(pathogenic cold)。
②欲如运枢:欲:《太素》上有“志(spirit)”。运:《太素》作“连”并注:“连,数也”(rapid by nature)。阳气通贯不止,动如枢机(the spirit will be disquieted the dredging defense Qi moves rapidly in nature)。
③起居如惊:王冰注:“卒暴也”(sudden onset)。
④神气乃浮:阳气失和而致神不宁(his spirit and Yang Qi excrete outside and the defense Qi become unstable)。
【解读】
(一)风寒之邪加重“目不瞑”之“卫气独卫其外而不入于阴”的病机进展
寒邪致病的特点,《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寒伤形”,又说“寒胜则浮”。王冰注:“寒胜则阴气结于玄府,玄府闭密,阳气内攻,故为浮。”张景岳注“寒胜者,阳气不行,为胀满浮虚之病”。此条经文“因于寒”,临床征象为“起居如惊,神气乃浮。”“起居如惊,神气乃浮”乃是神气不宁的征象,表明卫气主温煦是神气的表现形式,《灵枢·胀论》说:“卫气之在身也,常然并脉,循分肉,行有逆顺,阴阳相随,乃得天和”。《灵枢·营卫生会》说:“营卫者,精气也,血者,神气也,故血之与气,异名同类焉”。又《素问·举痛论》说:“寒主气收”,可知寒邪凝滞的特点更易损伤卫气主温煦的功能,从而出现血气不和,神气不宁的临床征象。此“因于寒”显然与通常寒邪致病征象有所不同。《灵枢·邪客》指出“卫气独为其外,行于阳,而不入于阴”是“邪气客于人”而致“目不寐”的基本病机,寤寐节律失调皆由卫气之行失常而成。尽管风寒外侵可导致神气不宁,但这并不意味着风寒之邪与“目不瞑”存在因果关系,可以肯定的是风寒之邪会加重卫气之行独卫其外的病情。临床上当失眠症状逐步改善时常常突然失眠加重,或彻夜难眠,或睡2~3小时而易醒。醒后难以入睡伴烦躁不安,合并用桂枝15g、炙甘草12g,失眠症状显著改善,诚如《灵枢·邪客》说:“适神不散,邪气得去”!如果有表证,疏风散寒后微微汗出,但失眠症状加重,此时处方中不能减去疏风散寒药物,加大桂枝用量则睡眠可以得到迅速改善,这也正是选择此条经文的临床意义所在!《伤寒论》伤寒施于火针误治以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治疗“烦躁”的病证,大塚敬节曾用此方治愈突眼性甲状腺肿患者因灸法治疗后,出现严重心悸并导致失眠的病例。可见仲景所说的“烦躁”与经文“起居如惊,神气乃浮”互文见义。这些病证均支持“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when Yang Qi brings its delicate function into play,it nourish the vitality internally)。”(《素问·生气通天论》)的结论。
(二)“起居如惊,神气乃浮”征象的病机分析
“起居如惊”是“寒主收引”导致机体行为动作的应激反应方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说“寒伤血”,《灵枢·营卫生会第十八》说:“营卫者,精气也,血者,神气也,血之与气,异名同类”。故“神气乃浮”是指机体受寒邪之侵所致气乱于卫,血逆于经而致血气离居,即血气不和的病证。“寒主收引”“寒伤形”皆是机体受寒邪之侵的发病特点。皮、肉、筋、脉、骨皆为其形,“寒伤形”的病位不离乎皮肤玄府、腠理的开合,筋膜弛张,经脉拘挛和骨痛阴痹。“寒主收引”的病机在《素问·举痛论篇第三十九》解释说:“寒则腠理闭,气不行,故气收矣”。显然“收引”是指卫气不行,揭示卫气行于三焦的环路既有筋膜拘挛,又有气涩不畅,表明胆气疏泄和敛降功能失常,故寒邪伤气的病位不离乎胆。又说:“寒伤血”,《灵枢·本神第八》说:“肝藏血,血舍魂”。寒伤血,血不舍魂,则“神气乃浮”。同篇下文曰:“阳气(卫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提示邪伤卫气既有筋膜失养,又有神不守位,可知寒伤血气病位在肝胆!这在《素问·痹论第四十三》所说:“肝痹者,夜卧则惊,多饮数小便”也找到辅佐证据。提示慢性失眠患者伴有夜尿频数,其病位在肝,且夜卧不安者更易外感寒邪!
关于“起居如惊”引发的临床问题就是“胆气不足(gallbladder vacuity)”。“胆气不足”可做两方面理解:①指精神心理的病证,如“心虚胆怯”。这不是此条经文所讲的内容,搁置不论。②胆疏泄和敛降功能失调的病证,这是此条经文讨论的内容,分析如下:
《素问·六节藏象论》说:“凡十一脏,取决于胆。”故胆失疏泄和敛降不及的病证具有虚实错杂特点,且内伤或外感的征象复杂。《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第四》说:“胆病者,善太息,口苦呕宿汁……心下澹澹,如人将捕之”。显然经文说的“胆病者”是指胆的疏泄和敛降功能失调。“心下澹澹,如人将捕之”是痰饮病的证候,《灵枢·五癃津液别》说:“三焦出气,以温分肉,充皮肤,为其津,其留而不行者为液”。其病机为胆失疏泄,敛降不及而致气化障碍,气机逆上,三焦津阻气滞则津气升降转输失常,揭示胆气疏泄、三焦气机升降皆是津液气化转输不利的主要病机。又《素问·六节脏象论》说:“津液相成,神乃自生”,故“虚烦不寐”为痰饮病证津阻气滞病证之一,《诸病源候论》说“若但虚烦而不得眠者,胆冷也”,由此可知,胆气不足指胆失疏泄,敛降不及,其津气通滞无不与三焦病变相关,因此,津液失调所形成的痰饮病证多伴随卫气不行,神气不足的症状,如精神不爽,头目昏沉,身倦怠,心悸动,夜寐不安,善恐,夜尿频且小便不利等。因此,《中藏经》增加了“头晕、不能独卧”,《医学入门》增加了“虚怯昏泪、不眠善恐”。通用教材阐述胆气不足的一般症状,除夜寐不安外,其伴随症状包括疲劳、口干、眩晕、心动悸、脘痞、腹满。
【经验方】柴胡桂枝干姜汤合温胆汤化裁
姜半夏9g 生薏苡仁20g 黄连6g 竹茹12g 茯苓15g 陈皮9g 枳实9g 柴胡12g 桂枝6g 干姜9g 天花粉12g 炙甘草6g 生牡蛎15g 炒酸枣仁15g 远志9g
目标证候:眠差善恐,不能独卧,胸膈郁热,心悸不宁,疲劳,面红,口干苦,脘痞或腹满,舌质红,舌根苔厚略带黄色,也有舌无变化者。
(一)方解
处方药物配伍重在恢复胆疏泄敛降和三焦津液气化转输功能,从而取得“津液相生,神乃自生”的目标疗效。以柴胡桂枝干姜汤和解散结,宣化痰饮;以黄连汤清上温下,和胃降逆;以半夏合薏苡仁取仿半夏秫米汤之义;以温胆汤理气化痰,清胆和胃,《经方医学》说:“尽管温胆汤用了黄连、竹茹等寒凉药却冠以'温胆’之名,此处的温胆并非温补之意,所谓'胆寒’也是'吃惊’'寒意’,绝非'身体发冷’的意思。温胆的意思在于'使胆气温’,而不是用温热药温之。”《王绵之方剂学讲稿》说:“胆的特点是既不宜热,也不宜寒,只有保持常温,少阳之气才能正常地升发,才能帮助脾胃消化。'虚烦不得眠,此胆寒也’。在这种情况下,更主要是因为少阳之气不升,脾胃的消化功能不行,产生痰饮,才用温胆汤治疗。竹茹是治疗虚烦不得眠的好药,它是清虚热的药,但它不是寒性,同时能和胃祛痰,止呕逆,除痰之后,胆气就升了。”
(二)临床应用
寒邪虽不是“目不瞑”的直接病因,但经文“欲如运枢”表明“因于寒”机体卫气振奋而抵御寒邪外侮。因“寒主收引”导致卫气不行、筋膜拘挛而呈现“起居如惊”征象,其病机主要在气乱于卫,血逆于经,血气离居,其证候皆呈现“血气不和”的临床征象,故“神气乃浮”揭示卫气行于阳,不入于阴的病机,此与经文“阳入阴,阴出阳”失常而致“不得卧”“目不瞑”病证相同。经文强调寒邪致病的病机为“寒伤血”和“寒主收引”,表明病位不离肝胆三焦,“因于寒”的病证包括津阻气滞,血气不和,筋膜拘挛征象,这与第5条虚邪贼风所致“目不瞑”并不完全相同,但机体受邪而致的卫气病变是其相似之处,由于卫气病变是发生寤寐节律失调的潜在病因,故经文说“神气乃浮”而不说“目不瞑”。临床治疗慢性失眠过程,经常遇到疗效不稳定的问题。虽然影响因素复杂,但寒邪引起慢性失眠疗效不稳定的事实已经得到临床充分证实。
以眠差善恐,不能独卧为主证,以烦热心悸,易疲劳,面红,口干苦,脘痞为次证。临床征象既有胆失疏泄而敛降不及致善惊易恐,不能独卧,面红,口干苦,舌红,又有津阻气滞,痰热内扰而致易疲劳,胸膈郁热,心悸不宁,脘痞或腹满,舌苔根垢,色略黄。证候多见于不规律使用西药镇静剂,初期使用或有效,久而用之疗效甚微,甚至出现抑郁精神障碍,查阅其治疗史可知,虽有眠差善恐,不能独卧,但屡投镇静安神之味却难收寸效;改辙以化痰清热,脘痞不得豁然,却又添胸膈烦闷,致使夜寐不得安卧迁延不愈。因病机重心在胆失疏泄,津阻气滞,故“清、疏、通、利”是治疗慢性失眠的有效方法,但治疗过程特别须注意合并胃气不和证候。若腹胀痞满较为突出,先予以黄连汤加木香、枳实、郁金、莪术、香附治疗1周,则腹胀痞满症状改善,且夜寐善恐,不能独卧亦得到程度不同的缓解,继之黄连汤合柴胡桂枝干姜汤化裁治疗,夜寐不宁、善恐症状可得到显著改善。维持治疗40天,寤寐节律的自我调节亦可得到基本恢复。
四、气乱于卫,津阻气滞导致慢性失眠气血逆乱的证候错综复杂
【经文】
8.少气时热,时热从胸背上至头,汗出手热,口干苦渴,小便黄,目下肿,腹中鸣,身重难以行,月事不来,烦而不能食,不能正偃,正偃则咳甚,病名曰风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阴虚者,阳必凑之,故少气时热而汗出也,小便黄者,少腹中有热也。不能正偃者,胃中不和也。正偃则咳甚,上迫肺也。诸有水气者,微肿先见于目下也……水在腹者,必目下肿也。真气上逆,故口苦舌干,卧不得正偃,正偃则咳出清水也。诸水病者,故不得卧,卧则惊,惊则咳甚也。腹中鸣者,病本于胃也。薄脾则烦不能食。食不下者,胃脘膈也。身重难于行,胃脉在足也。月事不来者,胞脉闭也。胞脉者属心而络于胞中,今气上迫肺,心气不得下通,故月事不来也。(《素问·评热病论篇第三十三》)
【注释】
①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邪:邪气(pathogenic factors);凑:聚集(accumulation)。此乃倒装句,非邪凑则气虚之谓,言气所虚处,邪必凑之(The accumulation of pathogenic factors is mainly due to the deficiency of kidney Qi)。
②真气:“真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充身”(Combination of innate essence with food nutrients produces genuine Qi that nourishes the whole body)。
③惊:惊悸(fright palpitation)。
【解读】
(一)风水病证之疑点解析
临床多从风水病解读肾小球肾炎综合征引用这条经文,经文所述“目下肿”可见于肾炎综合征典型征象,其余征象在肾小球肾炎综合征并非常见。尤其是病名曰风水,但体征仅仅是“目下微肿”,其原因经文强调是“水气”,这与仲景所阐述的水气病中的风水截然不同。分析如下:
1.“ 汗出”和“目下肿”对于“风水”病证而言,是一个与肾脏病临床矛盾的问题,因为“风水”虚实错杂,以水肿为标,其征象以面目鲜泽,身体洪肿,汗不出,仲景说“汗出乃愈”。显然,经文所说的“风水”病,并非临床水肿病中的风水证候。
2.虽然经文所说的水病为“诸水病者,故不得卧,卧则惊,惊则咳甚也”,但风水病或“有水气”仅仅提到“目下肿”,而且是“目下微肿”,并没有谈到面目身体四肢皆肿,反而着重提及其他临床征象,如“少气,时热从胸背上至头,手热,小便黄,口干苦渴,腹中鸣,身重难以行”,又有“咳甚,不得卧,卧则惊,月事不来,烦而不能食”,其病机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阴虚者,阳必凑之”,病机的特点在燥热内盛,气虚津亏。《金匮·水气病脉证》“不言水,反言胸中痛”与经文阐述水病征象十分相似。仲景所说:“病者苦水,面目身体四肢皆肿,小便不利,脉之,不言水,反言胸中痛,气上冲咽,状如炙肉,当微咳喘。胃家虚烦,咽燥欲饮水,小便不利,水谷不化,面目手足浮肿,其水扬溢,则咳喘逆。”其病机特点为阳气虚损,中气不行。张琦撰《素问释义》说:“水病肺肾为主,而实本于脾,盖肾为水脏,以类相从。故凡水责之肾,肺主治节,气虚不化,亦令积水。然苟中土气实,升降不失,则水无从生,故水病悉由脾虚不能制水也。”可知经文所说的水病或“有水气”并非是水肿病,而是津阻气滞,津液转输出入障碍的病证。
3.“ 腹中鸣者,病本于胃也。薄脾则烦不能食”,经文明确指出脾运胃纳升降失调是发生水气病的主要病因。继之经文又自训“不能正偃者,胃中不和也,水在腹者,必目下肿”。经文指出“目下微肿”为“水气”,但“身重难以行”的病因却是“胃脉在足”!经文自训为“舌干,少气时热,手热,小便黄”,这是水为热阻,决渎之令不行,阳气化为实,阴液化为结,阳实阴结,则肺气不能通调水道,水气迫肺而咳出清水。故经文又说:“气上迫肺,心气不得下通,故月事不来也”。
4.“口苦,不得卧,卧则惊”常见于胆失疏泄,津阻气滞,津液不行留而为痰饮所导致的眠差善恐,不能独卧的病证。故经文说“诸水病者,故不得卧,卧则惊”。
5.“少气,时热,汗出”,仲景称这种现象为“卫气不与营气谐和故也”。其“时热从胸背上至头,汗出手热”征象皆分布在少阳三焦经,这些征象是三焦为卫气之行的环路涩滞不畅,气乱于卫,津阻气滞所致。
6.“月事不来”并非仲景所说的水气病血分证的“血结胞门,其瘕不泻,经络不通,名曰血分”,而是“胞脉闭,心气不得下通”,由于少阳三焦经“布膻中,散心包”,故三焦津阻气滞,肺气上逆而咳清水,惊则咳甚;又因胆失疏泄而致口苦,不得卧,卧则惊。可见心气不得下通是由于胆失疏泄,胆气上逆,肺失治节而致胞脉闭,月事不来。
复习经文,此条经文所说的风水病与肾脏病临床风水病完全不同,故对经文所说“风水”病证提出了下述疑问:
1)“ 少气时热……身重难以行”与大承气汤证颇多相同之处。森立之注:“少腹有热者,即胃中有热之谓……《素问》所云'少阴者肾经也’即为仲景所云阳明证,经文唯以部位言之,不分阴阳二证”。
2)风水与《素问·水热穴论》《素问·风论》《素问·奇病论》和《灵枢·论疾诊尺》中风水、肾风不同。此条经文所述的临床征象在不寐、郁证、心悸等病证中更易多见。
3)“ 不能正偃者,胃中不和也……惊则咳甚”。目下为胃经,胃中不和则水道不利,知腹内有水气之候,以水在腹,故真气上逆,口苦舌干。此正是小柴胡汤之“或咳或渴,少阳病之口苦口干”,“可与小柴胡汤,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濈然汗出而解”。咳而吐出清水者即是水饮之所为,若仰卧则其水气凌心,故为惊也。此正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为水饮上迫心肝,发为惊证。
4)“ 烦不能食”与“食[插图]”(能食而倦怠乏力)不同;胆气不足者,食欲尚好,烦而能食,此证与胆气不足亦不同;烦不能食,月事不来是指心烦、不得眠、倦怠、食欲不振。
有鉴于此,原来此处的风水与仲景所说的风水根本不相关!虽病名相同,但并不是相同的疾病。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条经文是创制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的原始思路,但“病名风水”仍然存疑待考。研读经文不能仅仅局限于文字层面的解读,正如在《灵枢·卫气失常》中,仲景发现了痰饮病的临床特点,并提出“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的观点,创制了肾气丸和苓桂术甘汤!
(二)气乱于卫,津阻气滞是慢性失眠临床征象错综复杂的原因
诸多内伤杂病合并慢性失眠是临床经常遇到的问题。病因不同而慢性失眠病证相似,病因相似而睡眠障碍的临床征象表现不一。由于寤寐节律自我调节机制失常,五脏不和与慢性失眠相互作用,因此,睡眠障碍和五脏不和在慢性失眠的自然病程中往往表现为互为因果的发病特点。由于慢性失眠促进内伤杂病慢性迁延,加重内伤杂病临床进展,影响内伤杂病的治疗效果,甚至内伤杂病宿疾治疗无效,因此,改善寤寐节律的自我调节机制是阻止内伤杂病迁延进展的重要措施。
经文所述“目不瞑”“卧而有所不安”“不得卧,卧则惊”“瞋目”“夜不寐”虽皆见于不寐病证,但其形成机制有所不同。“卧不安”“不得卧”的病机重心在胃气不和;“卧则惊”“瞋目”“不得安卧”的病机重心则为胆失疏泄,津阻气滞,筋膜弛张;“夜不寐,昼不精”病机重心在气血两虚或精血虚损。揭示析因辨证是慢性失眠临床实践的重要方法。慢性失眠临床征象错综复杂,临床征象集中表现在两方面:一者以脾胃不和为主的征象,如烦而不能食,食不下,胃脘阻膈,脘痞腹胀,小便数而不利,便秘;二者以肝胆失于疏泄,筋膜弛张为主的征象,如头昏沉,胸中满而有堵塞不通感,焦躁易惊,烘热多汗,心悸不宁,身体倦怠,重则身动不随,肢体屈伸不利,这两组征象都错综表现在慢性失眠的临床过程。经文反复指出“卫气常行于阳,而不入于阴”和“目不瞑”病证的发生发展存在相关性,《灵枢·卫气失常》揭示,卫气失常是机体可发生水液、痰饮病证的主要病机,同时又强调二蹻脉渗溢气血的调节功能失调是睡眠障碍呈现诸多征象的原因,但津气通滞,筋膜弛张是慢性失眠发生发展的关键环节。
“不得卧,卧则惊”与上条经文所述“起居如惊,神气乃浮”证候相似,脏腑病位均涉及肝胆三焦,津阻气滞,但二者的病机和征象有所不同。上条经文为“起居如惊,神气乃浮”,所言“惊”尚未发生,是“因于寒”而致“欲如运枢,起居如惊”,继之加重“神气乃浮”所形成的“目不瞑”病证。此条是“不得卧,卧则惊”,所言“惊”已形成,为“风水”病的征象之一,是因“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阴虚者,阳必凑之”。病证的重心在胃气不和,病变涉及心肺肝脾,病机以阳明燥热、气虚津亏为主,兼以胆失疏泄,津阻气滞为特征。这种气乱于卫、津阻气滞为特征的病证中,经文反复强调“不得正偃”“不得卧,卧则惊”,揭示“目不瞑”是其主要临床征象之一,其病机为胃气不和,三焦气化失常,胆失疏泄而致津液转输出入失调,此乃机体因津气违和而“津液相成,神乃自生”机制失常所致的病证。经文所述风水病临床征象错综复杂,“少气时热……舌干……食不下者,胃脘膈也。身重难于行,胃脉在足也”皆为阳明燥热津伤,胃失和降的征象。“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并非劳倦内伤所致气虚证,而是肝失疏泄,胆气不升,脾失运化而致的肝郁脾虚病机。“阴虚者,阳必凑之”并非精血虚损所致的阴虚阳盛,而是由于卫气常行于阳,津阻气滞,津液失去濡润而致的气虚津亏病机。由此可知,此条经文指出“不得正偃,胃气不和也”,又说“真气上逆,故口苦舌干,卧不得正偃,正偃则咳出清水也。诸水气病者,故不得卧,卧则惊”,均强调“不得卧,卧则惊”“不得正偃”均属于自然入睡和自然睡眠状态均发生障碍的临床征象。由于寤寐节律皆源于二蹻脉功能状态,且太阳膀胱经、少阳胆经和三焦经的津气通滞及气血盛衰皆与二蹻脉缓急密切相关。经文所述“风水”实乃津气病变,揭示卫气行于三焦环路涩滞,筋膜弛张导致气乱于卫,津阻气滞是慢性失眠发生发展的重要机制,津气通滞状态是产生诸多睡眠障碍征象不一的重要因素。
【经验方】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伤寒论》)
柴胡18g 黄芩9g 清半夏9g 太子参15g 茯苓12g 桂枝12g 龙骨20g牡蛎20g 大黄6g 生姜9g 大枣6枚
一般不用铅丹。
目标证候:体征肥胖,彻夜不眠,夜眠易惊,胃脘胀满,惊惕不安,肩凝,手足麻木,浮肿。舌质红,舌苔黄白,干燥,脉沉涩而有力。
临床应用:经文说:“津液相成,神乃自生”。少阳三焦乃津液气化场所,又内合于厥阴心包,此条经文指出:“诸水气病者,故不得卧,卧则惊”,表明胆失疏泄,敛降不及,三焦气化不利则津液为病,因津阻气滞而致心神浮越,出现眠差易惊,夜寐不宁,不能独卧临床征象。肝胆气郁化火为烦,逆气上冲则惊,“食不下,胃脘膈”乃阳明燥热。胃中有火,水结肠间则腹中鸣,脾气被困不能上行津液则口干舌燥,肠间因水阻气不行而便秘,经文称“病本于胃”。气乱于卫,津阻气滞所致慢性失眠征象可见于诸多内伤杂病证候,例如,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围绝经期、绝经期综合征,代谢综合征合并慢性心肾损害,高血压病,脑动脉硬化和部分脑肿瘤等病证。这些内伤杂病并发慢性失眠的共同病机为胆失疏泄,敛降不及,气机升降失调,以致三焦卫气环路涩滞不畅,气乱于卫,筋膜弛张拘挛,津液转输出入障碍,津阻气滞而呈现津液病变,或为痰饮,或为水液,或为痰浊。由于彻夜不眠,久治不愈,逐渐出现头脑昏沉,或头痛,眩晕,心悸不宁,神思不清,多语,性情急躁,眼睑浮肿,背部灼热感,手足麻木,胸腹满闷,烦而不欲食,肩凝症,小便数而不利,便秘。因此,诸多内伤杂病并发慢性失眠的征象呈现错综复杂的特点。
内伤杂病属于五脏不和而引起三焦津气逆乱,气郁津凝病证,治疗的重心在升清降浊,利气行津。彻夜不寐,夜寐易惊,焦躁不安的基本病机是气血津液盈虚影响肝系之膜,调气行津须兼顾筋膜弛张病机。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证候为“胸满,烦惊,小便不利,谵语,一身尽重,不可转侧。”此方与柴胡桂枝干姜汤相较,此方无寒证,多水气,胸满、心悸不宁、惊惕不安皆是水气所为。水气不去,故一身悉肿,气乱于卫,筋膜拘挛,故为一身尽重,不可转侧。李文瑞主编《经方化裁·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说:“凡属神经精神方面的病态,属热证实证,或偏热偏实证,用他药无效,均可用本方观察治疗。”矢数道明认为:“本方为实证方,应介于大、小柴胡汤之间,胸胁苦满,心下部有抵抗。心下部膨满,腹部多见脐上动悸,因腹主动脉跳动亢进所致之腹部神经症状,即所谓上冲、心悸亢进、不眠、烦闷等,易惊、焦躁易怒、易动感情、善太息,甚至出现狂乱、痉挛等症状,小便不利,大便偏秘为目标。主诉一身尽重,动作不灵活,难以转侧,身动乏力,浮肿,麻痹等也为目标。”《类聚方广义》说:“治狂病,胸腹动甚,惊惧避人,兀坐(发呆而坐)独语,昼夜不眠,或多猜疑(嫉妒),或欲自杀,不安于床者。”《古方药囊》说:“胸中满而有堵塞不通感,焦躁易惊,小便难,胡言乱语,身体倦怠,重则身动不随,于大病中亦发生此证,不素气郁甚,亦发此证者,大便秘结为甚。”
第四节 夜寐不得安卧与肺失治节,胃中不和所致气血失和密切相关
一、胃肠虚满有序更替节律失调夜寐不得安卧
【经文】
9.不得卧而息有音者,是阳明之逆也。足三阳者下行,今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阳明者胃脉也,胃者六腑之海,其气亦下行,阳明逆不得顺其道,故不得卧也。《下经》曰:胃不和则卧不安。(《素问·逆调论三十四》)
【注释】
①不得卧:不能入睡(falling to sleep)。
②息有音:呼吸音嗄(hoarse breath or breathe with adventitious sound)。
③六腑:泻而不藏的器官(six hollow viscera which are of discharge but no storage)。
④《下经》:古经名(the Lower set of Classic)。
⑤胃不和则卧不安:胃中不和而难以入睡(the disharmony in Yangming meridian results in restless sleep)。
【解读】
(一)胃肠虚满有序更替是维系“五脏安定,血脉和利,精神乃居”的重要因素
经文指出“胃者六腑之海,其气亦下行”,若其气不下行,则“不得安卧而息有音”,其病因为“阳明之逆”。表明邪在胃则卧不安,邪在肺则卧而息有音。虽然经文没有指出引起“阳明之逆”的病因,但经文自训“胃者六腑之海,其气亦下行”,又说“胃不和”,则提示此“阳明之逆”是指胃和大肠。正如《灵枢·平人绝谷第三十二》说:“胃满则肠虚,肠满则胃虚,更虚更满,故气得上下,五脏安定,血脉和利,精神乃居,故神者,水谷之精气。”揭示肠胃满虚节律有序更替是机体精盛、气足、神旺的基础因素。若胃肠满虚有序节律失调则气不得上下,五脏不得安定,血脉涩滞,神气乃浮!又《素问·通评虚实论第二十九》说:“五脏不平,六腑闭塞之所生也。”尽管经文没有指出“阳明之逆”的原因,但由“不得卧而息有音”得知,此“息有音”乃气道有阻而致肺气不利征象。《素问·咳论》说:“肺咳之状,咳而喘,息有音。胃咳之状,咳而呕。”王冰注:“肺藏气而应息,故咳则喘息而喉中有息。胃之脉,循喉咙,入缺盆,下膈,属胃络脾,故脾咳不已,则胃受之也。胃寒则呕,呕甚则肠气上逆。”此可以佐证“息有音”乃是肺气不利,但由于非内外寒邪所为,故不咳;其次,“胃不和”亦非胃寒所为,又非胃腑壅滞,故不呕,故“阳明之逆”的病证中,经文没有说咳嗽、喘息、呕吐征象。由此可知,气不得上下,五脏不安定的原因是六腑闭塞,胃肠虚满有序更替的节律失调,大肠失于传导而致邪逆在肺,故令人不得卧而息有音!诚如张景岳说:“阳明上行者为逆,逆则气连于肺,而息有声,此胃气不降也。”重温经文,我们得到如下启示:
1.如果“胃不和”理解为胃气上逆,为什么经文只提及“不得卧”,而没有提到胃气上逆的其他临床表现?《素问·评热病论》在论述风水时,由于胃中不和可以引起诸多临床表现,包括“不得正偃,胃中不和”,但都没有提到胃脘胀满、呕吐、哕逆等症状
2.如果“胃不和”是指脾运胃纳失调的病机,在经文其他篇章内多次提及胃病的临床表现,例证:①《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第四》:“胃病者,腹[插图]胀,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膈咽不同,食饮不下”。②《灵枢·师传第二十九》:“胃中热则消谷,令人悬心若饥,脐以上皮热,胃中寒,则腹胀”。③《灵枢·胀论第三十五》:“胃胀者,腹满胃脘痛,鼻闻焦臭,妨于食,大便难”。④《灵枢·四时气》:“饮食不下,膈塞不通,邪在胃脘”。上述胃病例证中都没有提到“不得卧”。由经文可以得到启示:此处的胃不和更恰当的临床内涵是胃气“不得循其道”,胃肠虚满有序节律失调,而不是指脾胃纳运水谷功能障碍的胃肠道疾病!
3.马莳注释“阳明之逆”:“此言人有逆气诸证,有关于胃者,有关于肺者,有关于肾者之不同也。言人有不得卧者,是不安卧也。而鼻息呼吸喉间有音,其故何也。乃胃病者也。胃者,足阳明也。凡足之三阳,其脉从头走足。今足阳明之气逆而上行,故息有音”。可知逆气诸证有肺、胃、肾之别,“不得卧”是指不安卧,并不是强迫体位而不得卧。
4.《 灵枢·玉版第六十》:“胃之所出气血者,经隧也,经隧者,五脏六腑之大络也”。表明:“气积于胃,以通于营卫”。若胃阳明之逆气上行,则气乱于卫,营气不得独行经隧,则筋膜弛张拘挛,胃中不和是病证表现的部位,而不是指胃纳脾运升降失调的病机。陈潮祖教授认为经隧为筋膜,其研究结论为“肝系筋膜,本属脑系,脑外膜络即为心包络”。“不得卧而息有音,此阳明之逆也”是因筋膜弛张拘挛,卫气独行于外,不得入于阴,营气虚,故目不瞑!
(二)“阳明之逆”的临床征象
“息有音”是否为喘息?森立之说:“今逆而上行,不得从其道,则胸间必生饮为喘,故不得平卧。不得平卧者,乃倚息之谓也。《金匮》中云'咳逆倚息,短气不得卧,其形如肿,谓之支饮。’是也”。这个注释仍有疑问:首先,将“息有音”与仲景所说的“支饮”视为相同的病证,支饮属于饮停气闭,故内则咳而气逆倚息不得卧,外则其形如肿。
与经文“不得卧而息有音”病证不同。其次,若是胸间生饮,胸中为气街之道,气街有阻,则其人短气,饮留则津液凝滞而作渴。四肢诸阳之本,阳气从胸布达,饮随气溢,则四肢筋膜历节痛。仲景指出:“胸中有留饮,其人短气而渴,四肢历节痛”。因此,胸中生饮是气道有阻而非气闭,故其征象为“短气”而不是“咳逆倚息不得卧”。第三,“不得卧”马莳注:“不得安卧”,也不是森立之所说的“不得平卧”,可知“息有音”不是指喘息。
“息有音”本是气街之道有阻,但经文却说是足阳明逆而上行。《灵枢·刺节真邪第七十五》说“气积于胃,以通营卫,各行其道,宗气留于海,其气下注于气街,其上者走息道。故厥在于足,宗气不下,脉中之血,凝而留止。”这段经文明确指出,足阳明之逆引起“息有音”是由于宗气不行,气乱于卫,血脉涩滞,胸中气街之道有阻而致肺气不利!显然足阳明之逆属于“厥在于足,宗气不下”,其病证与胃气上逆不同。由于“不得卧”的主要病机在“胃不和”,因此经文反复申明说:“阳明者胃脉也,胃者六腑之海,其气也下行,阳明逆不得顺其道,故不得卧也。”“息有音”属于“胃不和则不得卧”的或然征象,而不属于“不得卧”的主证。进而言之,“胃不和”即使有胃气上逆相关的噫气、哕逆、呕吐征象,由于呕甚则败胃气,其临床征象往往是“安卧”,而不是“不得卧”,况且“胃气不和”病证并不是一定都有失眠的临床征象。阳明之逆所致宗气不下,筋膜弛张,气道有阻引起的病证除“息有音”之外,亦或伴有心血瘀阻的病证。临床用半夏泻心汤治疗胃下垂、萎缩性胃炎、胃肠神经官能症、窦性心动过缓、冠心病、心肌炎,屡屡获得疗效的事实亦提供了相关的佐证。半夏泻心汤治疗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获效的事实初步证实马莳注“不得卧而息有音”为“不得安卧”和“息有音”是符合临床的。这从《伤寒论》生姜泻心汤条文中提到“胃中不和”,处方后注“半夏泻心汤,甘草泻心汤,通体别名耳。生姜泻心汤,本云理中人参黄芩汤,去桂枝、术、加黄连,并泻肝法”亦得到印证。半夏、生姜、甘草泻心汤通过辛开苦降以消除心下痞证的机制属于泻肝法。由此可知,半夏、生姜、甘草泻心汤的病机在肝失疏泄,肝胃不和,条文所说的痞证中的“胃中不和”不是指脾运胃纳升降失调的病机,而“胃中”是指肝胃不和征象的表现部位。
【经验方】和胃调气饮
黄连9g 黄芩9g 白芍6g 香附9g 木香6g 生槟榔9g 桂枝6g 当归12g 川芎6g 红花6g 僵蚕9g 太子参12g 炙甘草6g
目标证候:头晕,心烦不得眠,甚至彻夜不眠,郁闷烦躁,逆气上冲,心中懊恼,泛恶嗳气,多疑善忧。舌质边尖红,舌两侧白苔,脉不定。
(一)方解
宗气不行,胸中气道有阻,胸中郁热,烦躁,故以黄连、黄芩苦寒以泄胸中邪热,以香附解郁,木香、槟榔降气散郁,皆以辛温之品以行气解郁,以太子参、甘草益脾胃之气。其药物性味苦辛的配伍方法与半夏、生姜、甘草泻心汤组方相似,所不同的是病机以阳明逆气上行而不是痰饮水液,故以辛温芳香解郁,降气之品取代干姜和半夏,佐以当归、川芎、白芍、红花、桂枝养血柔筋通络;尽管僵蚕与半夏皆有祛痰作用,但僵蚕解筋膜拘挛通络更适宜证候的病机。芩连配伍归芍芎效仿于黄连阿胶汤中芩连配伍胶、芍、鸡子黄,均为苦寒清胸中邪热,虽都配伍血分药,但和胃调气,病机以逆气上冲,胸中郁热而不得眠;黄连阿胶汤血热心烦失眠,津液枯燥,黄连阿胶汤应用目标:矢数道明说“因血热而心烦不得眠,主诉失眠、烦躁、颜面潮红、兴奋、心悸亢进、头重、头晕眼花、胸中烦闷郁热等,虚证用泻心汤类”。
(二)临床应用
阳明逆气上行是“不得卧而息有音”的病机主要特征。“胃不和”一者指中焦脾胃部位;一者指脾运胃纳的病证。“不得卧而息有音,是阳明之逆也”并不是指胃气上逆的脾胃病证,而是由于肝失疏泄,肝胃不和,筋膜弛张,胸中气道有阻,宗气不得下行,血脉凝涩导致的病证,病机的重心在“阳明逆不得顺其道”。由于“不得卧而息有音”的病机重心在阳明之逆气上行,故以和胃调气,养血柔筋是取得疗效的关键措施。
应用指征以“不得卧”以彻夜不眠,郁闷烦躁为主证,阳明逆气上行的征象以逆气上冲,头晕,胸闷烦躁,甚至胸闷如窒息状,心中懊恼,泛恶嗳气,多疑善忧多见。多见于40~50岁女性患者,清瘦体型,平素身倦乏力,不耐疲劳,经带尚无异常。情绪烦躁程度较重的临床表现与焦虑、抑郁病证相似。临床过程间歇性有脾运胃纳升降失调的心下痞,腹胀,呕逆胃肠病征象。使用解郁、化痰、安神、潜镇法治疗“不得卧而息有音”往往无效,尤其是彻夜不眠得不到纠正,情绪烦躁,多疑善忧,焦虑不宁愈加严重,有时给予较大剂量的硝基安定,夜间睡眠时间也只有2小时左右,醒后再难以入睡,甚至有轻生的念头。临证时,对于中年女性慢性失眠者,常遇到因逆气上冲而致烦热,有时口干,视物模糊,头晕较重,上方加钩藤20g、牡丹皮6g、麦冬15g,因中气不足,肝气侮而乘之,减去木香;但不得去掉桂枝,因小剂量桂枝可以条达肝气,且桂枝、丹皮平冲降逆效果较好。
二、夜寐不得偃卧与肺失治节关联性
【经文】
10.人之不得偃卧者何也?……肺者脏之盖也,肺气盛则脉大,脉大则不得偃卧。(《素问·病能论篇四十六》)
【注释】
①偃卧:正卧(lie on the back)。
②肺气盛:肺气逆满(evil Qi is filling abundantly in the lung)。
③脉大:胃脉大(dilation of the stomach meridians)。此处的“脉”指胃脉。《素问·评热病第三十三》曰:“不能正偃者,胃中不和”;《素问·逆调论第三十四》曰:“胃不和则卧不安”。张琦注:卫气之出入,依乎胃气。阳明逆,则诸阳皆逆,不得入于阴,故不得卧。
【解读】
(一)肺主治节参与寤寐节律自我调节机制
以往文献对“不得偃卧”解读为肺气壅塞所引起喘息不得平卧,这便产生一些疑问:
1.如果“不得偃卧”解读为由肺气壅滞所导致喘息病证的强迫体位,那么一定有咳喘症状。但是经文没有提及咳喘病证,而是说“人不得偃卧”?
2.“ 不得偃卧”的病机为“肺气盛而脉大”,按照《素问·脉要精微论》说:“大则病进”,“脉大”当为邪盛正虚,“不得偃卧”应属于危重病证,经文没有说“邪气盛”而是说“肺气盛”?
3.在阐述“不得偃卧”病机时,经文没有提到“肺主治节”,而是说“肺为脏之盖”!《灵枢·九针论第七十八》说:“五脏之应天者肺,肺者五脏六腑之盖也。”肺主一身之气,故为“脏之长也”,心主一身之血脉,故为“五脏六腑之大主”,表明“肺者五脏六腑之盖”并非是特指“肺为至高之脏”的部位而言,而是揭示肺主卫气、心主营血的气血关系,故《素问·痿论篇第四十四》说:“肺者,脏之长也,心之盖也”。又《素问·病能论》下文说:“气之通天也”,由《素问·生气通天论篇》可知,此肺气盛当指卫气盛而非邪气盛。卫气盛而脉大应是“不得偃卧”的病机?
4.经文明确说“脉大不得偃卧”,没有说“肺气盛而不得偃卧”?显然,“不得偃卧”并非由于肺气壅塞所导致喘息病证的强迫体位!“肺气盛则脉大,脉大则不得偃卧”与《灵枢·口问第二十八》说:“阴阳相逆,卫气稽留,经脉空虚,血气不次,乃失其常”文异而义同!经文明确指出“脉大”是“不得偃卧”的直接原因,因此,有必要说明“脉大”与“肺气盛”引起“不得偃卧”的临床意义。分析如下:
1)《素问·平人气象论篇第十八》说:“一呼脉再动,一吸脉亦再动,呼吸定息脉五动,闰以太息,命曰平人”,揭示出呼吸节律与脉动节律的谐协关系。
2)《素问·脉要精微论篇第十七》说:“脉者,血之府,长则气治,短则气病,数则烦心,大则病进,上盛则气高,下盛则气胀,代则气衰,细则气少,涩则心痛。”揭示诸病脉象反映的是判断机体气血失调轻重程度的指标,同时,《素问·平人气象论》说:“脉无胃气亦死”,表明诸病脉象揭示的是胃气盛衰。
3)《灵枢·邪客第七十一》说“宗气积于胸中,出于喉咙,以贯心脉,而行呼吸焉。”可知宗气是“肺气盛”和“脉大”之间联系的重要环节。故宗气的盛衰与肺主治节、心主血脉的功能直接相关。宗气主持机体呼吸节律、心脏搏动节律、心脏搏动迟速的自我调节。
4)由于诸病脉象反映胃气盛衰的程度,“胃不和则卧不安”“不得正卧者,胃中不和”皆指出胃气不和是“不得卧”的主要原因,同理,“不得偃卧”亦属于胃气不和的范畴。“脉大”则“病进”是因胃气虚乏而致病证加重而呈现“不得偃卧”的征象。
5)“ 气积于胃,以通营卫”表明胃气虚乏,宗气不足,气乱于卫,营气不行于经隧,故出现肺失治节,心不主血脉的病证。肺失治节,呼吸节律和呼吸频率失常,心不主血脉,心血瘀阻不畅,心不藏神,神气浮散。由此可知,经文所说“肺气盛”揭示的是宗气不行,血脉凝涩的病机!临床所见轻度入睡障碍通过减慢呼吸频率和深呼吸有助于进入睡眠状态。经文揭示胃气因和,肺主治节是维持自然睡眠状态和自然睡眠过程的必要条件!
(二)宗气不行所致呼吸节律自我调节失调是“不得偃卧”的病机特征
读此条经文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顺读为“肺气盛”→“脉大”→“不得偃卧”,逆读为:“不得偃卧”→“脉大”→“肺气盛”。若顺读,“不得偃卧”似乎是由于喘咳倚息不得卧的强迫体位,但经文可以直接说“肺气壅”或“肺气有余”或“肺病”等,却没有必要自训“脉大则不得偃卧”。因此,“不得偃卧”不是咳喘病证的强迫体位。若逆读,“脉大”则是“不得偃卧”的脉象,“脉大”的病机为“肺气盛”。由于经文论述的主要病证是“不得偃卧”,并不是论述“肺气盛”引起的咳逆倚息不得卧,因此经文自训为“肺气盛则脉大,脉大则不得偃卧”,表明“脉大”是“不得偃卧”证候的病机核心,“脉大”和“肺气盛”表明宗气行呼吸贯血脉功能失常。有理由认为“肺气盛”不是“不得偃卧”的主要基本病机。
中气足则宗气健行,宗气畅则气息均匀,这些均属于肺主治节的征象。《素问·脉要精微论第十七》说“长则气治,大则病进,上盛则气高,下盛则气胀”。王冰注:“夫脉长为气和故治,大为邪盛故病进”,可知“脉大则不得偃卧”是病进。由于诸病脉象是胃气盈虚的征象,故“邪气盛”的病位当属于“胃中不和”。“肺气盛”是因胃肠虚满有序更替失常,气不得上下的征象,如《素问·通评虚实论》说:“五脏不平,是六腑之所闭塞也。”可知胃气不和则五脏不安,血脉涩滞则神气乃浮!故经文说:“肺气盛则脉大,脉大则不得偃卧”。其次,肺气盛也不是吴昆注“上盛者,邪壅于上也。下盛者,邪滞于下”所说的病证。第三,肺气盛固然存在卫气病变,但卫气病变必然导致三焦津阻气滞,从而出现支饮、悬饮、溢饮、痰饮等病证。由于病机的重心在胃中不和,宗气不行,并不是说肺失宣降的卫气病变,且“脉大”也提示肺气盛的病机重心在宗气不行而不是卫气逆乱,故经文说“肺气盛则脉大”,而不是说“卫气盛而脉大”。虽然,脾失健运,湿阻中焦亦导致肺气盛,但病证不同。同篇下文说:“中盛、脏满、气胜、伤恐者,声如从室中言,是中气之湿也”。王冰注:“中,谓腹中。盛,谓气盛。脏,谓肺脏。气胜,谓胜于呼吸而喘息变异也”。张景岳注:“中,胸腹也。脏,脏腑也。盛、满,胀急也。气盛,喘息也”。此“腹中气盛”乃是湿阻中焦,水液上逆而致肺气壅滞。“伤恐”吴昆注:“伤,悲伤,恐,惊也。盖肺气不利则悲,湿土刑肾则恐,声如从室中言,吐气难而声不显。”《灵枢·忧恚无言第六十九》说:“会厌者,音声之户也。足之少阴,上系于舌,络于横骨,终于会厌”,肾气失守,浊邪留于会厌,故音声不彰。张景岳注:“是皆水气上逆之候,故为中气之湿证,此脾、肺、肾三脏失守也”。
经文论述不得偃卧的病机为宗气不行与胃中不和。“脉大”揭示胃中不和。胃中不和的临床意义是指不得偃卧,胃气虚乏,脾失健运,水谷化生精微不足导致宗气不足。脾不运化水液,津液在脾则湿热内生,加重胃肠虚满更替节律紊乱,由此而致气不得上下导致肺失治节。故宗气不行是形成肺失治节,呼吸节律自我调节失调病机的原因。由第6条经文解读可知,脾失健运是发生慢性失眠基础因素,湿热是加重慢性失眠的病理因素。由于脾运胃纳升降、肾藏化功能太过不及均有“五脏不安”的病证,脏腑功能太过不及,继发卫气病变而致二蹻脉渗溢气血失调是发生“目不瞑”病证的症结所在,所以,“目不瞑”病证与胃气不和密切相关,病程迁延可并发肾藏化功能异常的病证。
【经验方】清神益气汤(《脾胃论》)
茯苓12g 泽泻12g 苍术12g 防风6g 升麻6g 青皮6g 陈皮6g生白术12g 生白芍12g 生甘草6g 太子参15g 麦冬12g 五味子12g 黄柏6g
目标证候:反复变换体位也难以入睡,呼吸不畅,气短上气,食少乏力,脐周腹部胀满不适,大便不畅。舌质红,苔黄白略腻,脉寸关浮弦,尺沉。
(一)方解
“不得偃卧”的病机重心在“胃中不和”,病位在胃肠。“胃中不和”病机表现为胃肠虚满有序更替失调,一方面导致气不得上下则五脏不安,血脉凝涩则神气乃浮,另一方面由脾不运化水湿,津阻气滞而形成中焦湿热病理,此即经文所说的“津液相成,神乃自生”。因此分消湿热,升阳除湿是恢复胃肠虚满更替的有效措施,东垣说:“甲胆风也,温也,主生化周身之血气;丙小肠热也,主生长周身之阳气,亦皆禀气于胃,则能浮散也升发也,胃虚则胆及小肠温热生长之气俱不足”。故苍术燥湿健胃,黄柏清结热,苓泻渗其湿,升麻、防风升散郁结之气,故李东垣解释处方药物配伍时,称茯苓、升麻、苍术、泽泻、防风相伍功效为“此药能走经,除湿热而不守,故不泻本脏,补肺与脾胃本中气之虚弱”。以白芍、白术、太子参、陈皮、茯苓柔肝健脾,固守中气,青皮、陈皮通调气机,畅利胸膈。生甘草清热解毒,故东垣又说青皮、陈皮、生甘草、白芍、白术、太子参相伍,具有“此药能守本而不走经,不走经者不滋经络中邪,守者能补脏之元气”功效。佐以太子参、麦冬、五味子益气清肺,因胃气不和,肺失治节导致宗气不行,血脉凝滞,故以参冬益气复脉中之血气,则令宗气可以复原其行呼吸、贯心脉的功能。东垣解释麦冬、黄柏相伍时,说到“麦门冬之微苦寒,能滋水之源于金之位,而清肃肺气,复微加黄柏之苦寒,以为守位滋水之流,以镇坠其浮气。”
(二)临床应用
“不得偃卧”和“脉大”可见于慢性失眠病证。其临床表现为反复变换体位亦难以入睡,呼吸不畅,气短上气为特征,虽有咳嗽,但仅偶尔发作也是慢性失眠常见的证候。这种证候的临床特点是:以夜间难以入睡,反复变换体位,自觉呼吸不畅为主。食少乏力,脐周腹胀满不适,大便不畅并不与失眠同步发生,而是失眠超过2周左右才出现胃肠病证症状,治疗中表现为若睡眠差则出现食少乏力,脐周腹部胀满不适,大便不畅;若睡眠改善则这些症状随着消失。若以健脾和胃法治疗胃肠病证,食少、乏力、腹胀收效甚微,失眠不但未见改善反而出现胸闷不适。若使用养血安神之剂,反而出现彻夜失眠,纳呆、腹胀,口中异味,甚至酸腐秽浊,间歇伴随嗳气或呃逆。病情反复迁延不愈,甚至病程长达10余年。体格和辅助检查均没有发现异常表现。这种证候表现出夜寐不得安卧和胃肠道病证交替出现的特点,失眠促进胃肠道病证进展,而胃肠道病证则加重失眠。其中胃肠湿热病理是病机转变的关键环节。虽然清神益气汤与第4条益气安神汤证均有胃气不和的病机,皆以夜卧不宁为主症,第4条以气虚郁滞,脾运胃纳升降失调为病机重心;此条以胃肠湿热,宗气不行为病机重心,二者病机重心和证候有所不同。
第五节 邪淫于脏,气血两虚是夜寐多梦的主要病机
一、气血两虚是夜寐多梦的基本病机
【经文】
11.是以少气之厥,令人妄梦,其极至迷。三阳绝,三阴微,是为少气。(《素问·方盛衰论第八十》)
【注释】
①少气之厥:少气:脉气不足,指脉浮、虚、芤、迟、微、弱。厥:厥逆(reversal),五脏阴气不足而致厥逆(the critical reversal due to damage of Yin failing to hold Yang)。
②其极至迷:脉气不足,脏衰厥逆,阳不附阴而致梦魇(nightmare as extremity)。王冰注:气之少有厥逆,则令人妄为梦寐,其厥之盛极,则令人梦至迷乱。
③三阳绝,三阴微,是为少气:三阳:即太阳、少阳、阳明。三阴:即太阴、少阴、厥阴。绝(depletion)、微(faint)其临床意义相同,皆指脏衰引起的脉气不足。《太素》注:“至阳绝阴,是为少气”。
【解读】
(一)阴阳形气俱不足是“少气之厥”而致多梦的基本病机
夜寐做梦是寤寐节律自我调适的正常生理现象。“妄梦,其极至迷”则属于张景岳注:“五脏气虚,即阴不足也。所以为厥为梦者,皆阳不附阴之所致。”其病机经文明确指出为“三阳厥,三阴微,是为少气”,这种“少气之厥”属于久病阴阳两虚,而非《灵枢·口问》所说的“血气分离,阴阳破散,经络厥绝”。“少气”是指气息微甚还是指脉气不足,就成为解读“妄梦,其极至迷”病机和证候的关键环节。张琦注:“此盖屡厥日久,阴阳皆虚,百脉俱病,谓之阳证而又似阴,谓之阴证而又似阳,求之阳而非阳,求之阴而非阴,由五部脏腑否隔衰耗,气血无所征召,神志散越,若居旷野,若伏空室,气息微甚,绵绵若不能终日,久逆之候,有如斯尔。”同篇经文下文说:“形弱、气虚,死;形气有余,脉气不足,死;脉气有余,形气不足,生。”王冰注:“脏盛,脉气有余。脏衰,脉气不足也”。《灵枢·终始第九》说:“少气者,脉口,人迎俱小而不称尺寸也,如是者,则阴阳俱不足,补阳则阴竭,泻阴则阳脱。”进而言之,经文自训为“三阳绝,三阴微,是为少气”,明确指出是脉气不足,而没有说气息微甚。由此可知,“少气”是指脉气不足,而非指气息微甚的症状。因此将“少气”解读为“气息微甚”不符合经文所说脉气不足而致厥逆上行的病机。张景岳注:“三阳隔绝,则阴亏于上。三阴微弱,则阳亏于下。阴阳不相生化”。由脏衰而引起的“少气之厥”的病机表现两个方面:①阴阳气血两虚;②脏衰引起的厥逆。需要明确的是,脏衰引起的脉气不足并不是“脉脱”。脉脱有两种情况,其一脉脱为危重病证,如仲景说“脉脱入脏即死”。其二亦为危重病证,但脏衰并没有从脉象上有所反映,如张景岳注:“此其脉有所脱,而阴阳不全也”。虽然脏衰引起脉气不足表现为形肉有所伤,但与“形肉已脱”不同。张景岳注:“脏气未伤者,形衰无害,盖以根本为主也。又如《三部九候论》曰'形肉已脱,九候虽调,犹死’。盖脱与不足,本自不同,而形肉既脱,脾元绝矣,故脉气虽调,亦所不治,当与此节互求其义。”
(二)“清谷、亡血、失精”是“少气之厥”的主要病因
溯源其少气的病因,“少气之厥,令人妄梦,其极至迷”下文论述五脏气虚证所致诸多梦境,并总结其病机为“此皆五脏气虚,阳气有余,阴气不足。”张景岳注:“五脏气虚,即阴不足也。阴气不足,则虚阳独浮,故云阳气有余。无根之阳,其虚可知。所以为厥为梦者,皆阳不附阴之所致。”吴昆注:“若阳气有余,阴气不足,则当夕而梦。”表明五脏气虚所致诸多梦境的病机,其实质皆如景岳所说是属于“阴不足也”。与《灵枢·百病始生》说“忧思伤心;重寒伤肺;忿怒伤肝;醉以入房,汗出当风,伤脾;用力过度,若入房汗出,浴则伤肾”其病机自内而生于阴截然不同。由“三阳绝,三阴微,是为少气”可知,亡血、失精是临床常见“阴不足”的主要病因。经文同时强调阳气不足、阴气有余亦为“少气之厥”所致“妄梦,其极至迷”的因素,因此经文说“三阳绝,三阴微,是为少气”。吴昆说:“阳气不足,阴气有余,则当昼而寐”。仲景称作“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也……少阴病,脉微细沉,但欲卧,汗出不烦,自欲吐,至五六日,自利,复烦躁不得卧寐者死。”据此可知,仲景所说的“清谷”亦是形成阳气不足、阴气有余的主要病因。
与少气之厥形成诸多梦境相关的问题是与其相关的睡眠状态、睡眠时间异常。经文称自然睡眠状态为“夜卧”“夜寐”。经文中“安卧”不完全是指睡眠,常常是指“懈怠安卧”。《素问·平人气象论篇第十八》说:“溺黄赤安卧者,黄疸”。《灵枢·论疾诊尺第七十四》说:“安卧,小便黄赤,脉小而涩者,不嗜食”。就睡眠状态而言,“安卧”的临床内涵是指虽形似睡眠,但不是处于睡眠状态。因此,经文有“不得安”“有卧而有所不安”的明示。经文所说五脏气虚所致诸多梦境亦存在睡眠状态异常的问题。由于脏衰引起的脉气不足,故临床表现为“懈怠安卧”,虽安卧但属于似睡而非睡,夜寐多梦不宁的异常睡眠状态。“少气之厥,令人妄梦,其极至迷”与第3条“昼不精”“夜不寐”皆存在睡眠时间不足问题,但其病机截然不同,第3条经文也属于气血两虚候,其自然睡眠和自然觉醒的有序更替规律依然如常,“夜不寐”仅仅是指自然睡眠时间不足,但没有“少气之厥”的临床征象。
“妄梦,其极至迷”是由脏衰厥气上行所致,王冰注“其厥之盛极,则令人梦至迷乱”。厥气上行则可发生神志病证,实证则令人暴不知人,如《素问·厥论篇第四十五》说:“阳气盛于上,则下气重上而邪气逆,逆则阳气乱,阳气乱则不知人”。虚证轻则令人妄梦,虚极则令人至迷。由此可知,“妄梦,其极至迷”多伴有神志病证,即临床所说的神经症,其睡眠和觉醒的有序更替昼夜规律紊乱,昼夜均可发生睡眠多梦。以夜寐噩梦纷纭,梦中惊醒,心悸汗出,昼间神思不清,注意力分散,倦怠乏力为特点。仲景创制的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充分体现经文的临床意义!
【经验方】桂枝加龙骨牡蛎汤(《金匮要略》)
桂枝15g 白芍15g 炙甘草9g 生龙骨30g 生牡蛎30g 生姜9g 大枣3枚
目标证候:睡眠多梦,甚至出现做噩梦,梦中惊醒,心悸汗出,疲劳倦怠等。
临床应用:睡眠时间不足,卧不得安而多梦是慢性失眠常见证候,诸多梦境表现在慢性失眠的临床过程,其觉醒后多见神思不爽。尽管不同病证表现诸多梦境,其病机亦错综复杂,但神不守位是其基本病机。经文在不同篇章中反复强调由厥气上行引起神志病变。此条经文少气之厥,轻则令人妄梦,重者令人至迷,至迷为神志散越,其征象经文称为“若居旷野,若伏空室”。可知此少气之厥病机为脏衰引起脉气不足,厥气上行而令神不守位。《灵枢·营卫生会》说:“血者,神气也”,若血气未乱,经脉调匀,则令人神思清爽。《灵枢·本脏》说“人之血气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揭示脏衰引起脉气不足的基本病机在气血不和。《素问·厥论》指出,厥逆上行征象或令人腹满,或令人暴不知人。此少气之厥而令人妄梦,至迷,故其证候当有腹满征象。其病机核心在气血不和,经脉逆乱。其征象表现在神明之府(大脑)和脐以下腹部。清谷、亡血、失精皆可致气血不和。仲景说“阴头寒,目眩,发落”皆为厥气上行证候,阳气不降为下虚,发落为上实,乃因血并于上,瘀血聚于头部故也。脉极虚芤迟者,为下利清谷、亡血、失精的脉象。三者皆为气血虚衰,阳气衰弱之候。
经文说“少气”阴阳俱不足证候的治法为“如是者,可将以甘药,不可饮以至剂。”大塚敬节提出临床应用目标,摘录如下:“①小建中汤和桂枝加龙骨牡蛎汤证有很相似之处,两者均可用于时时出现或遗精、或手足倦怠、或口干燥等场合。②用于以精力减退、疲劳为主诉的病证,也用于遗尿、神经症、失眠症等。对阴茎和阴囊发凉、脱发等也有效。③可有足冷、头面烘热感,以及脐部悸动亢进、下腹部腹直肌绷紧突出等症状,脉浮大而弱,也可见弦小。④对于足冷、头面烘热感、头皮屑多等病变有效。”虽然天雄散方亦主失精家,其征象阳痿不举,遗精早泄,淫梦,腰腹冷,小便数,脐上动悸,脉见弱细,皆属于脾肾之阳虚衰,但经文强调“可将以甘药”而“不可饮以至剂”,故当与桂枝加龙骨牡蛎汤相区别。
二、起居无度情志失调是卧不得安而善梦的主要病机
【经文】
12.正邪从外袭内,而未有定舍,反淫于脏,不得定处,与营卫俱行,而与魂魄飞扬,使人卧不得安而善梦;气淫于腑,则有余于外,不足于内;气淫于脏,则有余于内,不足于外。(《灵枢·淫邪发梦第四十三》)
【注释】
①正邪:引起生理和精神活动失调的各种刺激因素(various pathogenic factors from the external that may stimulate or disturb the normal physical and mental activities)。
②定舍:固定的部位(fixed place)。
③魂魄飞扬:神不守舍(dispersion of the ethereal soul and corporeal soul)。
【解读】
(一)神不守位是令人卧不得安而善梦的基本特征
“正邪”既不是虚风贼邪,也不是外感六淫之邪。张景岳注:“正邪者,非正风之谓。凡阴阳、劳逸感于外,声色、嗜欲之动于内、但有干于身心者,皆谓之正邪,亦无非从外袭内者也。惟其变态恍惚,未有定舍,故内淫于脏,则于营卫魂魄无所不乱。因令人随所感而为梦”。可知正邪多源于起居无度和情志失调,“魂魄飞扬”表明正邪淫于脏腑而无定舍的病机特征是神不守位。同篇经文下文指出“十二盛”及“十五不足”皆可形成诸多梦境,表明梦境的形成与脏腑功能、属性、气之盛衰有关。马莳注:“阳气者,卫气也。阴气者,营气也”,并指出十二盛和十五不足皆是由邪气之扰而成。其次,环境因素所引起的情绪改变也是发生诸多梦境的病因,这些梦境多源于精神因素,往往会加重原发病的病情,甚至出现病情急性进展。故《素问·玉机真脏论》说:“忧、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矣”。经文揭示“正邪从外袭内,神不守位引起“卧不得安而多梦”的临床征象表现“气淫于腑,则有余于外,不足于内;气淫于脏,则有余于内,不足于外。”揭示正邪从外袭内所引起的神不守位属于虚实错杂证候。值得注意的是,“与营卫俱行,而与魂魄飞扬”,揭示“不得卧而善梦”的病机存在神不守位和营卫内乱两个方面。《灵枢·营卫生会》说:“营卫者,精气也,血者,神气也,故血之与气,异名同类焉”。然而,神躁不宁、神不守位皆与营卫内乱密切相关,如《素问·痹论》说:“阴气者,静则神藏,躁则消亡”。马莳注:“阴气者,营气也,阴气精专,随宗气以行经脉之中,惟其静则五脏之神自藏,而不消亡。若躁则五脏之神消亡,而不能藏矣”。表明营血与精神活动的相互依赖关系。血气不和则可导致神气散乱。王冰注:“人安静,不涉邪气,则神气宁以内藏,人躁动触冒邪气,则神被害而离散,藏无所守,故曰消亡”。揭示正邪从外袭内,起居无节,导致血气不和,神气离散。由此可知,“邪淫于脏,不得定处”即为气血不和。“气淫于腑,则有余于外,不足于内;气淫于脏,则有余于内,不足于外”揭示营卫内乱,神气离散,则令人善梦。若阴阳气血俱虚,则致少气之厥,妄梦,其极则至迷。诚如《素问·至盛衰论》说“起有所余,知所不足,度事上下,脉事因格”,吴昆注:“起,病之始也。有余,客邪有余也。不足,正气不足。言病之所起虽云有余,然亦可以知其虚而受邪矣。”王冰注:“度事上下之宜,脉事因而至于微妙。格,至也。”揭示“不得卧而善梦”的病机为邪从外袭,营卫内乱所致的气血不和。
(二)营血不足是脏腑受邪不得定处的主要病机
自然入睡、睡眠状态安定、睡眠时间适宜,自然觉醒后精力充沛,神思清爽是精血盈盛,血气谐协的外在征象。《灵枢·本脏第四十七》说:“人之血气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张景岳注:“人身以血气为本,精神为用,合是四者,以奉生,而性命周全矣。”虽然气血不和可以引起慢性失眠,但并非睡眠时间不足均有多梦妄梦的症状。从病史可以了解到诸多梦境皆与环境、情绪、心理等因素相关,慢性失眠伴随诸多梦境主要征象以睡眠时间不足,夜寐易醒,醒后神思不爽多见。“卧不得安而善梦”的病因为“正邪从外袭内,而未有定舍,反淫于脏,不得定处”。表明邪气之扰是导致机体睡眠时间不足伴随诸多梦境的主要因素,其中不适宜的环境和情景所引起的精神、心理和情绪以及寒邪是最多见的致病因素。虽病起于邪之有余,但亦反映营卫气血不足的内在因素,营血不足与脾肾胃肠功能失调密切相关。由于脾肾气虚皆可令五脏不安,经文称五脏为“神脏”,五脏不安则神无所归,魂无定舍,故卧不得安而善梦由此而生。《灵枢·本脏》说:“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也。”《太素》注:“脾肾之神志意者,能御精神,令之守身,收于魂魄,使之不散,调于寒暑,得于中和,和于喜怒,不过其节者,皆志意之德也。”从脾肾解读“志意”表明中气不固、精血不足是脏腑受邪而令魂魄飞扬的基础病机。故《灵枢·口问第二十八》说:“邪之所在,皆为不足”。经文“气淫于脏,不得定处”表明经文所说的脏腑是指气盛于卫气,气盛于营气。“气淫于腑,则有余于外,不足于内;气淫于脏,则有余于内,不足于外”揭示营卫之行失常导致不得卧而善梦的现象,与《灵枢·邪客》说:“夫邪气客于人也,或令人目不瞑,不卧出者,何气使然?……今厥气客于五脏六腑,则卫气独卫其外,行于阳,不得入于阴。行于阳则阳气盛,阳气盛则阳蹻陷,不得入于阴,阴虚,故目不瞑”文异而义同。故《灵枢·大惑论》提出,治此诸邪“必先其脏腑,诛其小过,后调其气”。此外,临床常常见到平素睡眠尚好的,遇到外在不良因素的作用而导致睡卧不安、夜眠多梦等,一般无需药物治疗,只要去除不良因素,其睡眠自然恢复如初。若长期不良生活和作息习惯,喜怒不节,情志所伤,则如王冰所说:“人躁动触冒邪气,则神被害而离散”。
【经验方】安神镇惊丸(《寿世保元》)化裁
当归12g 川芎9g 白芍12g 生地30g 酸枣仁15g 茯神12g 陈皮9g远志12g 麦冬15g 黄连6g 浙贝母12g 香附12g 胆南星6g 竹茹12g沉香6g 龙骨15g 清半夏6g
目标证候:夜寐多梦,睡卧不宁,时而惊悸,有如欲厥之状,头晕眼花,舌红少苔,脉沉细。
(一)方解
“不得卧而善梦”的病因重在环境、情景、情绪、心理等,表明气机升降失调是“正邪”致病的主要病机,换言之,气机升降失调亦是营卫内乱的基本特征。由于营气内乱表现为营血虚、卫气盛的特点。故清、滋、润是治疗营血虚的基本方法,故以四物、酸枣仁、茯神、远志养血益肝,宁心安神;而潜、纳、敛降是安神的主要方法,故以龙骨镇静,所谓“重可去怯”,沉香温而不燥,能降气达郁,摄火归原,二者并用潜镇摄纳;由于三焦是气机升降出入之所,“凡十一脏皆取决于胆”,故气机升降失调从胆三焦论治。胆失疏泄,敛降不及,三焦卫气之行环路涩滞,治法以清、疏、通、利为主,故以黄连、麦冬、竹茹清热安神;陈皮、清半夏、浙贝母、胆南星化痰散结;香附、茯神、陈皮行气解郁;对于证候复杂多变,《灵枢·大惑论》说:“先其脏腑,诛其小过,后调其气”,可知“诛其小过”贵在顾护胃气,以顾护中气温凉动静是调气之法的王者之道。无论是“邪气客于人”还是“正邪从外袭内”皆存在厥逆之气上行,而胃肠虚满有序更替,是气得上下,五脏安定的重要机制,故以麦冬、半夏降逆和胃。诸味合用获得安神镇静的疗效。
(二)临床应用
“正邪从外袭内,而未有定舍”揭示不适宜的环境和不良情景、情绪、心理、精神等因素是导致慢性失眠伴随诸多梦境的重要病因。正邪“反淫于脏,不得定处”表明并非是由脏腑病证引起“不得卧而善梦”,而是由于正邪引起营卫气血不和而致诸多梦境,故经文说“与营卫俱行,而与魂魄飞扬”,由于营卫内乱,进而引起脏腑功能失调,故经文说:“气淫于腑,则有余于外,不足于内;气淫于脏,有余于内,不足于外”。由此可知,营卫内乱是慢性失眠伴随诸多梦境病机的重要环节。需要指出的是,营卫不和亦是邪气客于人形成“目不瞑”的主要病机,如《灵枢·邪客》说:“夫邪气客于人也,或令人目不瞑,不卧出者,何气使然?……今厥气客于五脏六腑,则卫气独卫其外,行于阳,不得入于阴。行于阳则阳气盛,阳气盛则阳蹻陷,不得入于阴,阴虚,故目不瞑。”由此可知,“不得卧而善梦”与“目不瞑”皆属于慢性失眠的类证,而营血不足则是慢性失眠类证的基本病机!营血虚乏、神不守位则为“目不瞑”。营血虚乏源于胃气不和而水谷不化精微,这也印证了已经为多数人们生活实践反复证实的饮食不节和起居不适引起失眠等疾病事实。表明经文所说“正邪从外袭内”与“邪气客于人”文异义同,皆指出慢性失眠的致病因素包括六淫、情志、饮食、起居、精神心理等,从而揭示析因辨证是慢性失眠重要的诊治措施。
第六节 病例示范
病例示范1
王某,女,58岁,教师,太原市人。门诊病例。2012年5月13日初诊。
1.临床资料
主诉夜间入睡困难,彻夜合眼约2小时,头胀痛,耳鸣眼花6年,失眠加重2个月余。
起初仅以夜间睡眠时间不足,视觉疲劳,休息后始能缓解。6年前,因连年带高考毕业班课程,教学任务繁重,渐渐视觉疲劳加重,视物模糊,眼科拟诊“飞蚊症”,并出现夜间入睡困难,间歇性口服艾司唑仑片尚可维持夜间睡眠5小时,晨起后,颈项强,头轻度胀痛,耳鸣。此后不久,夜间入睡困难日愈明显,改服硝基安定后,仅能维持夜间睡眠2~3小时。遂就诊当地中医院,确诊慢性失眠,口服补肾、养血、安神之类治疗5月余,睡眠未见改善,视物模糊,头胀痛,耳鸣眼花依然如故。近2月失眠加重,有时彻夜难眠,头昏沉,手足清冷。经人介绍来门诊治疗。
望之体态丰腴,神情倦怠,刻下夜间入睡困难,夜间合眼约2小时,甚至彻夜难以入睡,头昏沉,耳鸣眼花明显。腰膝酸困,手足清冷,夜尿频,小便黄浊,饮食如故,舌质淡暗,齿痕舌,苔白,脉缓弱无力。否认心脑血管疾病、代谢及内分泌疾病史。
2.诊断思路
1)此非“阳气盛则瞋目”。“目不瞑”属于“生病夺于过用”,其征象指归肾气不足已朗照眉间,斯精血虚损垂可立焉,如何释此去之乎?《素问·上古天真论》说:“气脉常通,而肾气有余”,又第3条“老者之气血衰,其肌肉枯,气道涩,五脏之气相搏,其营气衰少,而卫气内伐,故昼不精,夜不瞑。”经文道出肾气不足尚存“气道涩”之几微,即气脉不得以常通。纯然滋补尤须兼顾气脉通涩。故治疗“目不瞑”,《灵枢·邪客》说:“决渎壅塞,经络大通”。
2)《素问·方盛衰论》说:“老从上”, 森立之注:“老年人脾肾自衰,心肺自盛者,以是为常,故曰从上。老人无病必宜如此。凡足弱膝冷便秘尿数,而耳目反聪明者,乃“从上”之义也。”因肾气不足,所以腰膝酸困,手足清冷,夜尿频,小便黄浊,但由头昏沉、耳鸣眼花则可识得十二经脉之血气皆不得上注于面的病机。由此而可以断定肾气不足,精血虚损乃是“目不瞑”的主要病机。
3)夜间入睡困难,甚至彻夜不眠,可谓之“目不瞑”矣。斯欲卧而不得卧,咨与第4条“有卧而有所不安”截然有别,亦绝非嗜卧而有所不安。虽神情倦怠,断然不是懈怠安卧。《素问·调经论》说:“志意通,内连骨髓”。《太素》注:“意是脾神,通于营气,志是肾神,通于三焦,原气之别使,皆以内连骨髓,成身形,及以五脏,故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由此可知,脾肾气虚皆可导致五脏不安,“魂魄飞扬,志意恍乱”。第4条经文说:“脏有所伤,及精有所之,寄则安”。
3.治疗经过
失眠历时5年余,甚以为苦,祈望能得一夜酣睡。可谓“目不瞑”矣,晨起头昏沉,整日耳鸣眼花,腰膝酸软,手足清冷缠身,可谓之“昼不精”,斯恰是第3条经文所说:“气血衰,肌肉枯,气道涩,五脏之气相搏,其营气衰少,而卫气内伐,故昼不精,夜不瞑”。良由肾气不足,脉有所结而下焦不通,经谓之“气道涩”,即气脉不得以通,血气不和,壅塞以积以聚,经络不得大通,徒以补肾养血难以奏效。又肾气不足,少火虚微,精虚无以化气,断无潜镇宁心安神之理。治法以补益肾气,决渎壅塞,令经络大通,所谓“疏气令调,则其道也”,遵《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精化气,气生精”,投以还少丹化裁:
熟地黄30g 枸杞30g 生山药15g 山茱萸15g 茯苓12g 石菖蒲9g远志9g 续断15g 五味子12g 巴戟天15g 肉苁蓉15g 炒杜仲15g 怀牛膝15g 小茴香9g 麦冬15g。7剂。
5月21日复诊:初始服药3剂,夜间已得入睡,但睡眠过程轻浅,服药至第5剂,竟然得以夜寐酣然,晨起神思清爽,精力充沛,腰膝酸困,夜尿频,手足清冷霍然而失,即使耳鸣眼花亦较前有所改善,如此疗效是始料未及的。维持原方不变,7剂。
5月30日复诊:慢性失眠已痊愈。耳鸣眼花亦改善,余无不适。再予14剂以巩固治疗。
4.临证心得
1)慢性失眠始因于劳神过度,营气衰少,卫气内伐,正如《素问·经脉别论》说:“生病起于过用”。“营气衰少”与“阴气虚”文异义同,故第5条说:“卫气独卫其外,行于阳,不得入于阴,行于阳则阳气盛,阳气盛则阳蹻陷,不得入于阴,阴气虚,故目不瞑”。肾气不足型慢性失眠尚有壅塞以积以聚,补肾养血之法固不可少,但补肾养血,莫忘决渎壅塞,如此可令血气和而经络得通,方可取得第2条所说“阴蹻阳蹻,阴阳相交”的疗效。
2)此案慢性失眠的证候特征表现为“昼不精,夜不寐”。若夜得以寐则昼得以精。故本在营气衰少,标在卫气内伐,显然,慢性失眠属于昼夜节律失调病证而不是神志类疾病。因此,治疗慢性失眠贵在恢复昼夜有序节律,如第1条经文所说“阳气尽,阴气盛,则目瞑,阴气尽而阳气盛,则寤矣”。潜镇安神并不是治疗慢性失眠一定不移之法。
3)此案所喜之处在于饮食如故,中气尚得以运化水谷津液,故可施以大剂量滋补肾阴药味,重点是使“阴本既固,阳气自生,化生精髓”,佐以小剂量辛温开窍,芳香辛味健脾,既可决渎气化之道壅塞以促进津气运行,又可疏浚经络,与滋补肾阴相得益彰,取得“大补心脾胃肾”的治疗效果。
病例示范2
王某,女,46岁,干部,太原市人,门诊病例,2016年8月10日初诊。
1.临床资料
主诉寐差多梦,头面烘热,胸颈以上多汗2年余。
2年前发现头面烘热,夜寐易醒,月经后期而来,经量多少不定,因呈间歇性轻度发作,自认为“更年期反应”,自行服用加味逍遥丸、定坤丹之类药物,自觉症状得以缓解。1年前睡眠障碍逐渐加重,夜间睡眠3~4小时则醒,且醒后难以入睡,由于睡眠时间不足,经常偏头痛,遂就诊当地医院,拟诊慢性失眠。遂以天王补心丹、养血安神片之类药物治疗,睡眠未见改善,继之间歇性服用艾司唑仑片维持夜间睡眠。半年前,寐差多梦,头面烘热,情绪易激动,胸颈以上出汗发作频繁,情绪紧张或进餐时,胸颈以上汗出如洗,手足胀满,月经后期而来,经量多少不定,色黯黑,遂就诊当地中医院,妇科检查未见异常,性激素检测促卵泡激素(FH)、黄体生成素(LH)皆轻度异常增高,雌激素(E)正常。妇科超声提示:前壁浆膜下肌瘤,大小2.1cm×1.6cm。临床确诊:围绝经期综合征,子宫肌瘤。证候诊断为阴虚火旺。因烘热、多汗,月经失调,转调经治疗,以滋肾清心,活血散结之法治疗5月余,夜寐多梦,轻浅睡眠,睡中易醒,醒后似睡非睡,烘热,多汗未见改善。此后自行服用定坤丹、八宝坤顺丸之类药物,病情迁延未愈,经人介绍来门诊治疗。
刻下:寐差或多梦,或入睡困难,或夜眠易醒,醒后难以入睡,双侧颞部头痛,头面时觉烘热,胸部以上汗出,急躁易怒,多语,肢体倦怠,手足胀满,夜尿频,小便不利。月经前后不定期,经量少,质地黯黑且夹有小瘀血块。脉弦有力,舌质暗红,舌苔薄白,根部垢浊。
2.诊断思路
1)烘热,多汗,烦躁易怒,不寐多梦,经量少,似可断为阴虚火旺。若是阴虚火旺型围绝经期综合征,予以滋肾清心之法,临证常可奏效,然则寐差,多汗,经量少却未见改善。
2)《 灵枢·五音五味》说:“今妇人之生,有余于气,不足于血,以其数脱血也”。《素问·腹中论篇》说:“有所大脱血,若醉入房中,气竭肝伤,故月事衰少而不来”。病程终始可见月经先后无定期征象,傅青主说:“妇人有经来续断,或先后无定期,人以为气血之虚,谁知是肝气之郁结乎!”双侧颞部头痛,烦躁易怒,肢体倦怠,小便不利,脉弦而有力亦确实与肝气郁结相关。
3)《 灵枢·禁服》说:“卫气为百病母”。张 景岳说:“凡人之寤寐,由于卫气”。卫气独行于外,行于阳,不入于阴所形成的卫气病变,既有致胆 气疏泄和敛降失调,又有三焦水道失调或气化不利,呈现津气同病和膜失柔和,并引起二蹻脉的纵缓、挛急,呈现“目瞋不合”或“目闭不开”征象。卫气病变并发津气同病、膜失柔和均可以发生慢性失眠。故《素问·六节藏象论》说:“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
4)寐差多梦是寤寐昼夜节律失调的表现,而寤寐昼夜节律更替与阴蹻脉、阳蹻脉功能存在关联性。《太素》说:“今于目眦言阴阳出入,以相交会目得明也。所以阳盛目张不能合,阴盛则目瞑不得开,宜取此二蹻”。故 张景岳说:“目之瞑与不瞑,皆蹻脉为之主”。
3.治疗经过
月经前后不定期,经量少,质地黯黑且夹有小瘀血块。疾疢弥久,所由来远矣,其咎安在?《素问·腹中论篇》“有所大脱血,若醉入房中,气竭肝伤,故月事衰少而不来”,由是则可以令肝气郁结,遂与冲任瘀阻攸关。爰肝之疏泄不及,役使胆气疏泄及敛降失调,三焦气化不利,津液出入失常,必然殃及卫气之行,悉致气郁津凝,冲脉为病而逆气上冲,于是有双侧颞部头痛,头面时觉烘热,胸部以上汗出,急躁易怒,多语,肢体倦怠,手足胀满,小便不利,脉弦有力,舌质暗红,舌苔薄白,根部垢浊。卫气之行纵然或迟或速,留于经脉导致三阴三阳经气血盛衰失调,已如气血渗溢于奇经八脉失常,若“沟陷渠沮”然,弥滋以甚,乃使二蹻脉或纵缓或挛急,胥以致睡眠与觉醒更替节律紊乱,或以瞋目,或以瞑目,乃见寐差或多梦,或入睡困难,或夜眠易醒,醒后难以入睡。论其治法,惟是“清、疏、通、利”,予以第2条定坤散化裁:
柴胡24g 黄芩9g 姜半夏9g 太子参12g 炙甘草6g 桂枝6g 牡丹皮6g 生白芍12g 生白术12g 泽泻15g 猪苓12g生地黄20g 生牡蛎20g。7剂。
8月20日复诊:药尽而令入睡转佳,彻夜梦减,夜尿频消失,晨起神情愉悦,手足胀满,尤以头面烘热,头痛,胸颈以上汗出改善殊甚!舌淡红,舌根部垢浊苔松化,虽气郁未尽得以通达,然此津行气化皆得益于疏瀹三焦,气机始以枢转,令卫气渐已行其常处。《素问·六节藏象论》说:“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上方加姜枣,合前方参术苓草,健运中气以鼓舞营卫之气。再进7剂。
8月28日复诊:睡眠易醒消失,偶有夜梦,夜间睡眠时间6小时左右,晨起神思清爽,昼间精力充沛,头痛消失。以往临近经期前1周则头痛,乳房胀痛,时下适逢经期前1周,头痛、乳房胀痛均未发作。自觉咽干,喜食辛辣,小腹胀满感,大便干结不调,排便困难,舌红苔薄白,脉弦滑有力。夙昔子宫肌瘤,虽血络倏尔通,忽而滞,概其恒有瘀阻无疑,时经期将至,愈易内生郁热,而令血气洋溢,所以气滞血瘀以经前期甚为明显,于是减半夏、牡丹皮,加天花粉15g、丹参15g 、夏枯草15g、益母草15g清热生津,祛瘀通经。再进7剂。
9月5日复诊:药进2剂时,经血来潮,经行畅,经色、量较上次周期有所改善。继续服药,寐安少梦,昼精夜寐有序更替节律恢复如初,自觉无不适。舌质淡红,舌苔薄白,脉弦有力。斯子宫肌瘤尚存,必自于血气不和,当是时,治法以调肝健脾,疏利血气:
当归15g 川芎9g 赤芍15g 生白术12g 茯苓15g 泽泻12g 香附9g乌药9g 五灵脂12g 牡丹皮12g 桃仁9g 桂枝9g 益母草15g 凌霄花12g。10剂。
9月16日复诊:自觉无不适,妇科超声提示子宫前壁肌瘤缩小至0.6cm×0.4cm。
4.临证心得
1)功能性月经失调是围绝经期综合征主要证候,其病机多见肾气不足,冲任失调。的确,此案性激素检测结果也提示考虑围绝经期综合征。尽管经量少,质地夹有瘀血块,似乎为经文所说的“血枯”证,但舌质暗红,舌苔垢浊,脉弦有力并不支持血枯证诊断。其舌脉征象却支持存在津液气化转输出入障碍病机,治疗效果亦证实了此案病机的确为气滞津凝。
2)《素问·六节藏象论》说:“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经文揭示气不和、津液不得相成是不寐发生发展的机制之一。三焦气化不利,卫气失常,气郁津凝,筋膜失养,阴蹻阳蹻之脉或缓纵或拘挛,临床征象或以瞋目,或以目瞑。正如张景岳说:“目之瞑与不瞑,皆蹻脉为之主”,又说“凡人之寤寐,由于卫气”,卫气独行其外,行于阳而不入于阴,由此可知卫气失调是寤寐昼夜有序更替节律紊乱的原因之一。
3)经文论及女性病证的气血特征时,《灵枢·五味五音》说:“不足于血,有余于气,以其数脱血也”。《素问·调经论》阐述血气不和时,临证有善忘善怒的征象。由月经前后不定,经血量少、色质瘀血块,子宫肌瘤,急躁易怒,舌质暗红,脉弦有力,可以得出肝失疏泄,冲任瘀阻的证候诊断。其主要病机是肝气郁结,三焦气化不利,卫气失常,津气失和。
20240920.xz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举报。短期股票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炒股股票配资平台太原市晋源区第十小学校迎来了朝气蓬勃的一年级新生
- 下一篇:没有了



